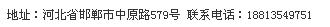风把麦粒留住许贵祥
图片摘自网络
当太阳偏西,偏到坠入山的帷幕之中时,逆光映照下的悬崖,便铺下来半场阴影来,燥热渐渐退去,当天三场中的最后一场麦子刚刚打碾完毕。人们将柔软而温热的秸秆搭在肥硕的草垛上,然后把碾压细碎的那些夹裹着麦粒的麦梗、糠皮、草屑弄倒一起堆积成半尺厚的长方形状在场的中央。卸去眼罩的一对黑牛灰头灰眼地迈着困乏的步子回去了,女人们拍打干净身上的柴草和灰尘离开了,还有一些男人们也陆续离开。而那些被称为扬场把式的男人们却不慌不忙地在阴凉中歇下来,吃烟,喝水,谝传。他们边歇边等,要等待一场风在傍晚时刻到来。
本来,风是无形无踪无影的,但在此后的一场仪式中要成为主角登台亮相。
看不出来哪儿有风的迹象,周围的树静静地,偶尔发出窸窸窣窣的窃窃私语,似乎在酝酿一场风的呼啸。当然,农民们此时的需求对野惯了的风是有些苛刻,偏要让风在规定的时间吹过来,这就得碰运气,看风是不是买账。过了一段时辰,那些被称为把式们的男人中间有人起身,拿起木锨将麦粒和糠皮的混合物抛在空中,抛得那样高,是要迎接风的到来吗?然而,那些麦粒和杂物劈里啪啦掉下来,原封不动。看来风还没有来,或者说风力还不够强劲。但那人并没有丝毫的失望,再次坦然地坐下来,仍然吃烟谝传。
稍许时刻,场边的树枝突然摇曳起来,是风来了,风说来就来。听说会扬场的人有咒语管着风,真实与否不得而知,但愿是真的,那样的话神奇就会永远保鲜。随着风起,席地而坐的男人们似乎被风吹动,纷纷起身,熟练地抄起木锨。五六个男人,纵排,一绺,和风的方向垂直交叉,以相同的力度和速度,用木锨将混杂的麦子和糠皮高高地抛在空中,一锨接着一锨,在空中画出一道道优美的抛物线来,木锨在风中翻动,风在木锨上缠绕,麦粒和糠皮在木锨上滑落。此时此刻的风,是那么的清晰可见,那么的具有方向性。在平常,风来了又去了,有时急促有时舒缓,谁都不留意风是具体而有形的,此刻,风显然是有形有力,像一位高超的技术工,眼睛明亮,手腕纤巧,工艺完美,熟练而有序地把麦粒和糠皮分拣开来,在优美的抛物线形成又散开的瞬间,麦粒挣脱风的手臂,垂直落下,沉沉地散落在风的身姿之下。而那些糠皮、麦壳、草屑、灰尘仍然缠绵在风的裹挟中纷纷扬扬,在约莫一两米或者更远一些三四米的地方,慢慢地漫下来。在如此反复地轻重缓急分明的节奏里,先是颗粒饱满的麦子落下来,然后是那些被糠皮包裹着的并未成熟的稗子紧随着落下来,然后又是那些叶片较大有一定分量的糠皮落下来,最后是那些细小轻微的糠皮和尘灰,轻轻地飘散在远远的远处。
风是活着的,这是风的一场演出,它与扬场的把式们之间有着深深的默契,把式是总指挥,风是主演,麦粒、糠皮、木锨、扫把在人和风的操控之下起舞、跳跃、奔跑、降落。随着木锨的起落,麦粒降落,糠皮飘扬,每到这时候,有一个头戴草帽,手握大扫帚的人匆促出场,穿越在草屑、糠皮、麦粒的帷幕之中,如同风雪之夜的赶场人。他利索而急促地挥动扫把,把那些和风较着劲,不愿离去的稗子糠皮扫过去,扫在麦子和糠皮的中间地带,让麦子更加干净,人们把这个环节叫做“净场”。这套完整流程在人们农业生产过程中应用而生并逐渐得以完善完美,也许,在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只有用如此的办法和手段让麦粒变得干净。难道,这就是艺术之舞蹈的最初蓝本和最终皈依吗?这是一个多么美丽有趣的场景,农人们在那样重复单调却又完美无缺的流程中感受丰收的喜悦和兴奋,而这样的喜悦和兴奋他们并不需要用歌唱或呐喊来表达,而是融化于他们的眼神、动作和力量之中。《诗经》中说 :“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时的手足舞蹈,来自农民们内心的丰收之情,喜悦之情,是与自然世界的翩翩起舞。
天色暗淡下来,扬得干干净净的麦子被装进粗蔴口袋架在骡马的背上,摇摇晃晃地回家——回到了生产队的仓库。收割之后,土地安静地睡去,粮食的回家是土地把礼物交给了侍弄过他的人们,从而结束了它一年来盛大的仪式。风和麦粒有着一生一世的不解之缘分,麦粒在春风里发芽,在夏风里抽穗,在秋风里饱满,又在这场傍晚的风里呈现出金黄灿烂的肌肤和容颜。扬场终结,风儿似乎也回家去了,回到树上,树枝挥手相迎,回到了屋顶,炊烟袅袅起舞;回到了山谷,野草忙乱了脚步。风走的时候,沾染了粮食的味道,那浓厚黏稠的麦香随着风的飘荡而走街串巷,香气弥漫在村子的角角落落,人们在风中嗅到了熟悉的粮食香味,让他们有了期待和欲念。再过几天,他们可以去仓库里分得一年口粮,农民把粮食叫口粮是多么的亲切和妥帖。是的,风留住了麦粒,留住的是人们的口粮。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