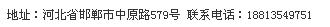简静岁月长薛老师七月课程小记下
(六)
本来薛老师这次来济南想讲韩信,这个人太值得一说了——这是个明眼人,才情与志气皆备,满蓄云雷,可惜智慧与心量不够,判断客观形势一向目光如炬,却从来没有看清过自己,“总被自己傲岸的姿态阻挡得只剩一片阴影。”
但后来薛老师考虑到这是第一次在济南开讲《史记》人物,还是应该让气象大的刘邦来开这个场。
读史记人物特别有意思,让我们可以看到与自己生命形态不同的人的好处。“看得到,就学得到。”
薛老师说,沛县出人物,其中一个原因,是沛县地理位置在南北之间,兼得南北之长。
但我和小伙伴们讨论的时候,还是觉得沛县之神奇不可思议:出了一个刘邦也就罢了,居然出了一个团队!
萧何、樊哙、曹参……都不是寻常人物。没有萧何负责后勤,刘邦和韩信的很多仗根本没法打,而且刘邦带军离开咸阳返回霸上时,萧何眼光长远,把秦朝的律令、图书全部带走,后来就是凭着这些,奠定了汉朝建国的基础。樊哙也不只是个有勇气的莽夫,刘邦曾经舍不得离开咸阳这个繁华都市,樊哙与张良一起劝谏,才让他还军霸上。不只是张良有见识,人家樊哙也不让呢。韩信后来落魄时,别人都不太搭理,唯有樊哙仍然敬他是个人物,见面必行大礼,即使韩信百般看不上他……
萧何病重将逝,向惠帝建议让曹参继任,以及曹参一听说萧何病逝就知道自己肯定是下一任相国、立刻收拾东西准备上任这一段,看得我特别的感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太美好了——“何素不与曹参相能”,我虽然跟你不和,不喜欢你,但我依然了解你的好,认可你的好。生死关头,我依然充分相信你。
之前他们不过是小吏、屠狗辈,怎么会有这么高的见识,这么洒脱的气象?刘邦也就罢了,人家是张良都要感慨“沛公殆天授”的人,那别人呢?他们的气象怎么来的?
薛老师说,其实这都是因为有刘邦。刘邦的气象大,就把他身边的人也带得气象大了。
(七)
司马迁称刘邦是“仁者”,“仁而爱人”,这评价非同一般的高。
“仁”是无隔,能感通到与别人成为一体;是“上与星辰近,下与庶人亲”。
这评价,不是从人情角度,是从天道的角度。
从人情的角度看,刘邦很多时候简直是“不要脸”,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就能看到他是个彻底自由的人。
看到秦始皇出巡,刘邦感慨,“大丈夫当如是也!”这才是大丈夫啊!这里面没有明确的目的性,表达的是羡慕和向往,带着好意的赞叹。这便是有“兴”。“兴于诗”,因为诗不传达具体的知识,看起来最没有用,其实是无用之大用,因为诗是用来调整生命状态的。
与刘邦形成鲜明对比的项羽,遇到同样的情境,他说,“彼可取而代之也。”这目标明确的语气,带着戾气,和从别人那里夺来什么的强烈的抓取心。
二者是全然不同的生命状态。一个人的生命状态,会成为他此后所有因缘的核心。
薛老师认为,论对于身外之物的随时能放下,刘邦与颜回的状态相近。利衰毁誉,称讥苦乐,他可以“八风吹不动”。
越到紧要关头,越有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清。他彻底无情,又有强大感知力、直觉力,兼得男女之长。
修行,到最后修的就是这个“有感而无情”。无喜怒哀乐,纯粹是干干净净的好感,就是中庸的“中”,是那个“喜怒哀乐之未发”。
“中”是天的境界。
我们是懂道理但做不到。刘邦是不懂这道理,但他就这么活着。是真正的“无所住而生其心”。面子、亲情、喜怒哀乐、生死,都无法束缚他、牵绊他。
修行到最高处,无非如此。
所以,在薛老师眼中,《高祖本纪》同于修行,读《史记》,能读出佛经。
修行第一阶段:是视人如己,看别人如同看自己。有理解与同情,感受到对方的状态,知道对方的有效性与有限性,知道对方的不得已。
第二阶段:看自己好像看别人。这是刘邦的境界。有感而无情的境界。也是天人之际的视角。
薛老师在新书《天人之际:薛仁明史记六记》中展开谈这一点,说得更详细。
“我一直觉得,如果一个读书人能懂得了刘邦,这个读书人的眼界与气象,肯定就会不太一样。”
“刘邦外表看起来没个样子,可实际上,却是真有本领、真有见地,尤其他那不沾不滞的能力,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人世间有许多事物在人的意念之外,是人力无法解决也没办法影响的,可是,事情偏偏又必然如此,这种人力所不及之处,在我们传统的用语,就叫作‘天’。现在假使有一个人,眼界或生命状态已经达到天与人的交界之处,这个人就变得不好理解,因为,你不能只用人的角度来看他。这样的人,你会觉得他不近人情、无法用常情揣度,可偏偏常常又是对的。司马迁的厉害之处,就在于碰触到了这一块。自司马迁之后,从班固写《汉书》开始,后代的史书基本就碰不着这一块了。为什么呢?从班固开始,所有写正史的人,清一色,通通都是儒者。儒家对于‘人’的世界,有其强大而坚定的秩序感,可对于‘天’这一块,却常常有隔阂。……他们解读事情时,通常会有个清楚的大是大非,也会有个清晰的道德观,但正因过于强调是非道德,反而受限于‘人’,‘天’这部分,就相对薄弱了。”
讲大是大非,如法海,道理都对,但不让人喜欢。人家没请教你,人家过得好好的,你自己非要自居正义地去教育、拯救别人,那是自以为是,是傲慢。
所以最好的诗是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里面没有“我”,没有道德是非,空山无人是我,青苔满路也是我。
(八)
《史记》中,常常出现“不祥”这个说法。祥这个字,从示,是从上天的角度来看事情。
有时,一个人充满好意地去做事,反而没有好结果。因为是从人的角度去看的。
前些天,我家老张同学眼皮上长了一个霰粒肿,发炎了,只好在眼皮内侧挨了一刀,做了个一个门诊小手术,把里面的东西割掉。
医院回家,路上他抱怨:现代科技怎么这么不给力,都能神州六号了,怎么还不能发明一个仪器,嗖的一下,把囊肿里面的东西吸出来?那不立刻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抱怨很好玩,就开始跟他分析起来——这个仪器现在当然不存在,将来也不应该存在。因为,长囊肿,说明身体的平衡出了问题,有了多余的热,多余的火。他的身体我知道,其实有寒湿,寒湿在内,所以郁火上扰,这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是生活方式不恰当,以及情志问题,让身体失去了平衡。
任何疾病,任何身体的状况和问题,都是上天对我们的提醒,告诉我们应该改变。如果,真的拜现代科学之赐,真有某个仪器,能迅速、无痛苦的解决病痛,我们还有改变的动力吗?肯定没有了。
所以,从人的角度,老张同学对病痛的抱怨是非常正常、合理的。
但从上天的角度,这种仪器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存在的。
病痛的存在,才是合天道的。
老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哈哈。
(九)
像我这样平时不太看《论语》、《孟子》、《墨子》等传统经典的人,反倒是特别喜欢听老师们聊这些,因为是借老师的窗口在看我平时看不到的风景。
薛老师谈到“以善服人,不如以善养人”,只是这话虽然是孟子说的,孟子自己却没做到,他给人一种是非过度分明的压迫感。
真正做到的是孔子,他说话的态度背后,不是修辞技巧,不是我们平常说的“口才好,会说话”,我们可以想象他带着浅浅的笑容说,“我们那儿跟你们不一样。”
他不会说“不好”,他只是说,“不一样”。
就像他如果去异地,有什么食物不合他的胃口,他大概不会说“这个食物好难吃”,他会说,“这个我吃不惯”。“吃不惯”,是更加接近事实的表述。
墨家讲兼爱、平等、刻苦、奉献,自我牺牲、薄葬、非乐。在春秋战国那个乱世,特别有道德感染力。
儒家讲的是常道,用久了不会伤身。而墨家,用久了会出问题。如同《神农本草经》把药草分为上中下品,上品主养命以应天,无毒,久服不伤人;中品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下品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
儒家传统强调本末先后,亲情比国法重要。这方面,又是孟子讲得最好——
桃应问孟子:如果舜这样的明君为天子,皋陶这样正直、铁面无私的人做司法官,遇到舜的父亲瞽叟杀人这样的状况,舜应该怎么办?
他如何在自己身为天子的职责、对下属尽忠职守的支持、以及对父亲的尽孝之间取得平衡?如果不能兼顾,他如何取舍?
孟子说:舜不会阻止皋陶把瞽叟抓起来,因为这是皋陶应该做的。但他会偷偷地把父亲救出来,然后“窃负而逃”,背着他逃到海边,“弃天下犹弃敝蹝”,跟老爸在海边过着快乐的日子,“乐而忘天下”。
这才“合乎人情”,才合乎中国人根底的思维。
儒家没有“大义灭亲”这回事,因为“灭亲”是最大的不义。真有人这么大义灭亲的话,这种人不能来往,因为他骨子里没有大信。
儒家的东西是中国人的大根大本。
有意思的是,前几天去山大听“现象学与天道”年会的讲座,其中讲到观卦的卦辞——“盥而不荐”。“盥”是祭祀之前洗手,“荐”是正式祭祀中献祭礼的仪式。意思是,祭祀的正式仪式不值得看,之前准备工作的默默洗手才值得看。孔子在《论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达。
为什么呢?因为正式仪典中大家都在扮演角色,只有假人而无真人,只有角色意识,应有的情感被遮蔽。没有本真的情感了。而儒家的大根大本正是在这里——不是形而上的东西,而是本真的情感。
正与薛老师遥相呼应。
(十)
平常心是道。
道,是人可以走的路。
大道至简,天底下的事情没那么复杂,复杂是因为我们读了太多的书,刷了太多的中科白癜风医院爱心公益白巅峰专科医院那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