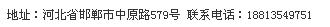朔方散文雍措凹村的风
雍措,女,藏族,四川康定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9届少数民族创作班学员。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星星》《四川文学》《西藏文学》《散文海外版》等刊。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现居四川甘孜。
凹村的风
说凹村的风之前,得说说凹村的样子。
凹村的左右都是山坡,各不相同,也不对称,有高有底,有急有缓,最后殊途同归,汇集在硬板子山上。硬板子山偶尔长些杂树杂草,不长草的地方,露出白花花的石板。上了年纪的人说,这山老了,患上了白癜风。不管是不是得了白癜风,硬板子山是凹村离天空最近的山,活在高处,过着神仙的日子。凹村坐落在两坡之间、硬板子山之下,既像硬板子山孕育的种,又像两坡中生长出的苗。但归结起来,坡和山本身就是连体,断胳膊断腿的事情,说出去看上去都是不好。我想坡和山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在日子里和平共处了下来,显得和和睦睦,招其他山体的羡慕。
有山体的呵护,凹村像宠儿一样,在其间活得安然,与世无争。
站在远处看,凹村又是坡和山的隔,这隔不深不浅、不长不短的立在那里。有了这道隔,两坡种植的果树完全不一样,这点在春秋两季尤其突出。春天,左坡的果树开花,右坡的果树还没有醒过来,等左坡花开得不想再艳了,右坡的又开始开了;秋天,右坡种的果树都是不耐寒的种类,叶子先黄,而左坡却绿油油的。活在凹村的人,记忆里总是觉得春秋在凹村待的日子很长很长,长得他们有时经常忘记还有夏冬两季的存在。
凹村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样,没说到位的,你再去问问每天镶嵌在天上的云朵、星星、月亮、太阳,它们无事可做,观察得一定比我细微。跑边的话不多说,我们要回到风的主题上。
凹村,风是有性格的。高兴的时候从左坡来,不高兴的时候往右坡来;特别憋屈的时候,从硬板子山来,顺变捎些小石子下山。小石子不争气,蹦跳两下,就被杂草荆棘给逮住了。
风,有没有同时从三面都来的时候呢?
“少,我活九十五岁了,只见过一次。那次,天阴得跟灶里的锅底灰一样,乌云压着地面,闪电发着怒火,一次次撕裂黑压压的云层。凹村生长在黑暗里,树枝发出折断的声音,木门用板凳抵着又被推开,窗户嗤嗤作响,房顶上的青瓦一片片被掀落下来,一朵朵黑云从有缝的缺口里钻进屋,寻找着什么。村人躲在柜子里和床下,大人捂住孩子的嘴,不让哭出声,生怕被黑云寻了去。过了一个晌午,风嘶叫的声音减弱了,凹村人悄悄从藏着的地方探出头来。天晴了,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地上乱七八糟的杂物,证实了刚才发生的一切。”老人说完,思想还停留在那场大风中,收不回来。
凹村的风,吹老了一代代凹村人,又迎来一个个新生命。它留给凹村人的不止是记忆,还有一些渗进骨子里的东西,抹不去,忘不了。
吼声
风,天生是捎信儿的种。在凹村,张溜子破沙沙的吼声,最能说明这点。
“眼睛大,嘴巴大,鼻子大,里里外外不消停。”不知道哪辈祖宗留在凹村的话,用在张溜子身上,简直是量身定制。张溜子的爷爷长成这样、父亲长成这样、现在的张溜子也长成这样。村人都说,张溜子家下的种干净,不像有些人家,不知道到哪一辈就长得祖宗不像祖宗、阿爸不像阿爸了。种纯,是夸奖张溜子家,他走在人前人后都为此很是得意。张溜子得意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遗传的破沙沙的嗓子。这样的嗓子养活了他的爷爷、阿爸;到他这里,又养活了他。当然,他心里亮堂着,除了遗传,他还应该感谢凹村的风,要不光靠嗓子的力气,是不够的。
张溜子的嗓子,对于在煤油灯下过日子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凹村人称张溜子吼声大哥。但凡凹村有婚丧嫁娶之事,都叫他来打理。以前也有几个凹村男人想当吼声大哥,可试过之后,不是喉咙破了,就是嗓子哑了。只有张溜子一直坚持着,而且越吼嗓子越亮堂。
张溜子说这都要归功于凹村的风,他是个会借风传信的人。
怎么个看法,他说只要他前面站着一棵有叶子的树就可以了。树叶左偏,风来自左坡,他的嗓门就往左吼;树叶右偏,他的嗓门就往右吼。风是有脚的,跑得比兔子还快,捎信的速度自然快。在风中,张溜子破沙沙的声音,越来越有味道。他知道哪个字被风带到哪里会绕个弯,那个字他就会拖得长长的;哪个字被风带到哪里,会窜进葡萄林,他就吼得粗些。“酒摆起,烟散起,远方的贵客,莫客气。鞭炮响起,筷子动起,宴席走起。”风把他的话,捎到每家每户的窗户里,不多一字,不少一字,凹村人总是能按着时间去赴宴。
风,有时颤悠悠的,张溜子的吼声也跟着颤悠悠的;风,有时急躁躁的,张溜子的吼声也急躁躁的。远近几个村子的吼声大哥,都没有张溜子的声音好听。
张溜子说他这辈子一直会走在风里,让凹村的风,养活他。
风的消息
每到收割麦子的时候,凹村人都盼着风。
风从右坡刮来,右坡的麦子摇摆着苗条的身姿,一个劲儿地往左坡扑,扑不过来的又等着下一场风。扑的痕迹,像流淌着一条条金色的河水。风,把成熟的麦子香味,带进村人的鼻孔里。风香了,凹村人开始张罗着镰刀、勒皮之类的家什。风越大,垂着头的麦穗离壳就越快,麦秆子也干得越快。
风,像听话的娃,没日没夜地吹,吹熟了庄稼,吹暖了凹村人的心。
收割的日子,太阳挂在空中,麦子在阳光下金灿灿的。凹村人的额头亮闪闪地冒着一颗颗汗珠子。风,翻越左坡,拂过麦地,盘旋在收割人的身边,汗珠子吹凉了,背心的热气吹散了。收割人拿着镰刀,站立在风中,会心地笑一笑;麦浪也跟着欢蹦起来,相互间发出哧哧的笑声。
妇人们在院坝中间,摆放好长凳;男人们抬出平坦的石板,架在木板凳上。麦穗跟着风一起走进院坝里。背麦穗的人,一股劲儿把麦穗倒在地上,风也跟着一屁股坐下。打麦穗的事情交给男人,背麦穗的事情让给妇人去做。男人在阳光下,举起一把把结实的麦把,啪啪啪地摔在石板上。麦粒脱壳而出,散落在院坝里、男人的身上。听着刷刷刷的掉落声,男人使的劲儿更大了,黝黑的肌肉一次次鼓起来,又一次次消下去。风一阵一阵地拂过,像抚慰麦粒的疼痛一样。
这个季节,凹村每户人家的高墙上,都用竹竿撑着一件小孩子的破衣服。凹村在秋季远远看去,人丁兴旺。
高墙上的破衣服,是用来观察风的动向。风从右坡来,凹村人就把撮箕里的麦粒,朝着风来的方向哗啦啦地倒下。风中,麦粒和壳迅速分离开来,麦粒掉在脚边,壳顺风吹走好远一截。看见高墙上的破衣服在风中改变方向,凹村人立马将掉在地上的麦粒和壳收拾干净,又重新端一撮箕杂粮,朝着风来的风向,哗啦啦地倒下。
好事的村娃们,有时趴在院墙上,风还没有来得及赶进院坝,就指着风来的方向大声喊:“风来了,风来了,风刮弯了梨树的顶。”村娃的话音刚落,端着撮箕的人多出了几个。风一来,一起哗啦啦地把麦粒倒下。有些人家上心的村娃,每天干着看风的事,麦粒也可以提前打整干净、尽早入柜。
凹村,人们把牛当人养着。但是,牛干不了的事,风却能干。风是不说话的人。
秋天,风的消息,对于凹村来说,很重要。
杨二的媒人
左坡刮过的风,细的时候,头到右坡了,尾还在左坡;右坡刮过的风,宽的时候,走到凹陷的地方,就走不动了,让左坡的果树伸着脖子等;风从硬板子山来,一般都是乱着身子,硬生生地冲到凹村公社的院坝里,吹得那面整天挂着的彩旗一个劲儿地嘚瑟,发出求饶声,才又绕着身子没头没脑地散去。
杨二信仰风,风是他的媒人。
右坡脚下,李表叔家养着一个姑娘李幺妹,二十岁出头,模样乖巧,针线活做得细致。村人传言:李幺妹绣搭搭帕上的凤,会飞;绣鞋垫子上的花朵,能发出真花的香味。眼下,李幺妹到了婚嫁年龄,远近村庄还没有娶上媳妇的男人们,就心慌得厉害。男人心一慌,媒婆们的脚就忙个不停。李幺妹家的门槛,都快被媒婆踩断了。
李幺妹很少出门,整天关在屋子里绣花。花是给谁绣的,李表叔弄不明白。李幺妹没啥文化,这和那个时代重男轻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她不怪阿爸。但是,她心里装着的东西丰富着呢,这从她绣的花花朵朵上就能看出来。她没有出过远门,只认识凹村的人。她不想离开凹村去和一个不认识的人结婚生子,她要守在阿爸身边,守着凹村过日子。不过,这些话她藏在心里,不好意思给阿爸说。
“提亲?给李幺妹提亲?俺心尖尖上都不敢想的事情。要长相,俺在凹村急着结婚的男人中间,排不上号;论家业,俺家除了一头会耕地的老黄牛,啥都没有,我就是站在山坡坡上看媒婆奔走的命。不过,俺命中有福。”杨二说。
说到这里,杨二抬起头,看着那片固央的玉米地,若有所思:“多亏那场风啊。”那场风,来得很乱,树左偏一下,右倒一下。吝啬鬼唐爪子家锅灶里飘出的炖野鸡味,被风吹得全村都是;仇人张娘和二蛋子家烟囱里冒出的青烟,亲亲热热地搅在一起,两家还全然不知。在风中,最起劲叫唤的是固央那片玉米林,像大渡河夏季涨水一样哗啦啦地来,又哗啦啦地去,一声比一声粗狂。“风来得急,我躲闪不了,放下背篓,坐在玉米林里,看着玉米秆稀里哗啦地倒下去;风一停,玉米秆又稀里哗啦地站起来,这声音很整齐,像训练过一样。这时,我听见玉米林里窸窸窣窣地响动起来,这和整齐的风声不同,接着前方的玉米林摇晃得厉害,心里生起一些可怕的东西来。我站起身,吼到:‘谁?’刚才摇晃得厉害的玉米林,停止了左右晃动。‘我来寻被风吹走的绣花帕。’一阵响动之后,是李幺妹出现在我眼前,玉米花的花粉沾在她头上,头发在风里有些乱,脸红红的。风还在一个劲地吹,密密的玉米林响动得更加厉害了……”有关那天玉米林的事儿,杨二说到这里,就不再往下说了。总之,李幺妹最后成了杨二的老婆。
“风是俺的媒人。虽然,俺没有像真正的媒人一样,在大喜的日子里给风送上一个猪脑壳。但是,俺会像供家神上的佛一样,对待风。”杨二说。
离奇的事儿
缺失的东西,让风补一补就好了。这是凹村人认定的理儿。
凹村的风,有治愈缺失的疗效。这话说到哪儿,或许都会成为笑话,但凹村人却祖祖辈辈记着。
左坡的根,源自大渡河的上方,地势平坦,且靠着东方,日照时间长;右坡的根,源自大渡河的下方,地势陡峭,且靠着西方,日照时间短;再因硬板子山的偏袒,左坡就更显阴凉了些。关于阴坡阳坡的说法,在日子过着过着的时候,就被凹村人认可了。
左坡日照时间长,自然就是阳坡了,右坡且为阴坡。阳坡的风,从平坦的地方而起,温温柔柔;阴坡的风,从陡峭的山崖而来,像刀子一样,刮得人脸疼。阳坡植被丰茂,阴坡植被矮小。说了这么多阳坡的好,却为啥在阴坡居住的人只见多,不见少呢?说来,不怕外村人笑话,这和风有关。
和风接触得时日多了,你就会明白,风是一件离奇的东西。它悄无声息地在你身上做着手脚,你却全然不知。在凹村,阳坡的姑娘往往只往阴坡嫁,阴坡的姑娘往往只往阳坡走。也有留在本坡或走出凹村的姑娘,但到最后都变得丑里古怪,不敢见人。
凹村人,爱凑热闹,就连种庄稼这样的事儿也不例外。凹村的土地,是凑着身子一坎一坎往下沿的,长短宽窄不一。谁家的人多,地就多。当然这样的多,并不是无底线的多。地分到一定时候,你家还有最小的人,就把他划成黑人了。黑人就是没有地的人。我就是我们家的黑人。凹村人不懂什么大道理,他们懂的道理都是外人觉得鸡毛蒜皮的事情,比如干活时不能将撅起的屁股对着别人的头。
阴坡阳坡的土地左右相连,为了避免干活时屁股对着别人,那就是只有头对着头做事。左往右走,右往左走,干农活干着干着就遇在了一起。遇在一起,大家不免相互坐在水沟边寒暄几句。日子就这样过着,时间一久,凹村人发现阴坡阳坡人的脸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阴坡人的右脸红润,阳坡人的左脸红润,只有两坡和在一起,看着才感觉是一张完整的脸。看习惯了,两坡人倒也不觉得别扭。可遇上全乡开会,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就露了出来。后来为了调和左右脸色不匀称,凹村就形成了阴坡往阳坡嫁、阳坡往阴坡娶的习俗。当然,这都是凹村姑娘们做的事情,男人们不在乎这些。所以凹村的男人是远近出了名的阴阳脸,他们丑到深处,爱恋的人却越来越多。
一些缺失的东西,用风补一补就好了。凹村人说的是女人们的脸。
[责任编辑漠月]
原载《朔方》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