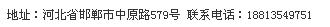假行僧时间尽头的酒店第4话
我好像从没飞过出笼子,而是拼命撞开铁索,冲进了另一座笼子。
系列短篇「时间尽头的酒店」第一季造纸街奇谈
第4话:假行僧
16
我花了好长时间才认出他。
面前这人大约三十岁年纪,精瘦,皮肤黝黑,胳臂上的青筋时隐时现。他穿了一件皱巴巴的汗衫,一条洗得发白的工装短裤,配上满是尘土的运动鞋与褐色长袜,简直令人忍不住发笑。还有那贴满时代符号的帆布背包,满不情愿地跨在肩上,我打赌已经用过十年了。
他刚要打招呼,看见我,瞬间愣住了。
“你、你是尹陆吧?”他显得很激动,“不认得我了?”
我一脸茫然,想不清楚这人究竟是谁。
“你忘记咱们在博卡拉的时候了?”
原来是他。想想也真是好笑,上回见到他,还是五年前。
这人是我同系的学长。当年在大学里的传奇人物,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他独自一人,四处闯荡,攒够了路费就立刻出发,既不停留,也无人相伴。就连学校的肄业通知单也没能将他召回北京。当初在学校,我只闻其名,从未与他正面接触过。直到毕业两年,我前往尼泊尔,在博卡拉见到了他。
那正是我意气风发的年纪,看见博卡拉的湖光山色,喜马拉雅山群峰如刃,横贯天际,就兴奋得不能自已,跟随一帮欧美老嬉皮挥霍度日,欢天喜地。直到快离开时,才碰巧遇到他。那天晚上,我们一伙人远足归来,月照银山,夜色撩人,老城郊区静悄悄的,神庙与石碓也陷入沉睡。路到半途,听见远处传来奇怪的乐器声,好奇心起,就往声音的方向走去。一座供奉婆罗门神明的小庙亮着微光,庙里的八臂神明样貌丑恶,宝相庄严。几个僧侣模样的人聚在小庙门前,拨弄乐器,迎声起舞,还有四个东亚人坐在一旁,闭目冥想,对我们这伙闯入者不闻不问。
众人随地坐下,围成一圈,讲起五湖四海的趣事,顿时有种世界民族大团结的错觉。有人在身背后问我:“你是不是在北京念书?”突如其来的中文着实吓了我一跳。我回头看他,没头没脑地说了句,我还以为你们是日本人或者韩国人。
他哈哈大笑,伸了个懒腰,像是刚刚返回这个世界。
“这三位是日本人。”他说。
他接着问我在哪所大学、什么学院、哪一届毕业,然后哈哈一笑,报出自己的名字。我没立刻表现出惊讶的态度,反而恍惚一阵,才想起来他就是那位传奇人物。
“你来这里多长时间了?”我问他。
“两个星期。我哪儿也不去,每天就待在这里。”
“待在这里做什么?”
“通过冥想,接触主宰,感受造物。”他故意作出一种冷静的姿态,仍然掩饰不住眼神因兴奋激动发出的亮光。我上下打量他一番,心里有点厌恶。
“盘腿坐好,像我一样。”他似乎看出我的不屑,冲我笑笑,凑过来拍拍我的后背,用拇指顺着我的脊梁向下捋了两遍。
“深呼吸,放松下来,感受自己体内的能量。”
夜色阑珊,旷野的风阵阵袭来,一刻也不停歇。
17
离开博卡拉的前一天,我又去了那座小庙。他果然在那里。看到我来,他显得很高兴,让我就地坐下,二话不说,开始冥想。这简直成了一种交流的方式。睁开眼睛,我问他离家有多久了,想没想过回去生活,安定下来。
他说,我从二十一岁起,开始断断续续地游荡,直到现在已经是第五年了,刚开始在国内,后来逐渐到国外,我不懂你说的安定下来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就很安定,你指的是结婚,然后养个孩子吗?我倒是结过婚,有过孩子,可惜孩子不是我的。
“你结过婚?”我有点难以想象。
“哈哈,是啊,我和前妻几乎是闪婚,当时最瞧不起那些爱情长跑的,我们认识两个月就领证结婚了。”他的口气倒很随意,“后来我不断出门,撇下她一人,行踪不定,终于激怒了她。她想尽办法不让我走,甚至趁我睡着,把我锁在家里,现金、钥匙、银行卡统统带在身上,还把我刚办下来的护照给撕了。”
“太疯狂了。”
“现在想想,也不能怪她,换成任何一个女人,都无法忍受吧。后来她告诉我,自己怀孕了,以自杀来威胁我。如果我再离开北京,她就和肚子里的孩子,一起了断。”
“这是报着必死的决心呐。”
他苦笑两声,拍拍我的肩膀,说:“兄弟你还年轻,不懂女人呐。她们为什么要拿你的错误去惩罚自己?一个每天出门都要化妆、站在镜子前挑选衣服、抱怨自己腹部赘肉的人,你相信她会自杀?爱自己还爱不过来呢!”
“那么怀孕也是假的咯?”
“当时我以为是。”他轻叹了一声,“我坚决不信她怀孕了。因医院检查的单据,她在我面前也没有任何反应。闹僵的时候,她连出门都不告诉我去哪里,我怎么能知道是真是假?”
“所以你还是逃出来了?”
“不错。我无法忍受那种生活,有点难以理解吧?”他抬起头仰望天空,继续说:“家里老人信佛,总去自由市场一笼一笼买麻雀放生。我小时候不懂事,喜欢养点小动物,就央求家里老人,不要都放生掉,留下十几只养起来。老人疼孩子,不忍心拒绝,就留下十来只关在笼子里,扔在阳台养起来。结果呢,我眼睁睁看着那些麻雀,不停地往笼子上撞,撞得头破血流,羽毛划破掉得满地都是,浑身血污,直到死掉为止。它们个头虽然小,性子却刚烈得很。从那以后,我也再也不养宠物了。受不了。”
“就这样走掉,没有逃避责任的愧疚感吗?”我迟疑片刻,补充说:“我不是在评判,只是觉得这两件事,概念有点不一样。”
他哈哈一笑:“没关系,这算什么,想想当时有多少人骂我。不光是她,还有我的朋友,家里人,都觉得我是个无耻混蛋。但是呢,责任这东西,得活着才能给予吧,总感觉那样子我活不下去。要说愧疚,那是当然的。整整一趟下来,我都心不在焉,在外面飘了不到一年就回去了。结果到家的时候,孩子已经出世了。”
“孩子不是你的?”
“她那时候很冷静,告诉我说孩子本来就不是我的,与我无关。我听了这话,火冒三丈,又觉得自己没什么资格指责她,满腔的悲愤、懊恼,像是有人往我脑子里打了一针,有东西蹿进泪腺,又酸又辣,眼泪顷刻就流出来了。她就那么冷冷地看着我,一句话不说,眼神都是漠然。后来我一气之下就走了,下定决心再也不回去。”
“她在报复你。”
“没错。她很久以前就计划好了。”他摇摇头,长吁了一口气:“不过我已经不在乎了。这五年在路上,我经历过不少人,也遇到过不少人,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点麻烦事,别那么纠结。与造物相比,人类简直太渺小了。”
他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那些怪事,满嘴都是神秘主义的论调。我听到半截,感觉心烦意乱,就谎称有事,与他告别。
18
这一别就是五年。
我绕过酒店前台,冲他笑,走过去握了握手,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一周前吧,意外收到了这个。”他将手里的邀请函递给我。
“我还以为你再也不回来了。”
“说来不好意思,我之前还回来过一趟,不为别的,就想看看他们母子俩。”
“放心不下?”
“还是明天再说吧,先让我睡一觉,我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最后一个问题,我登记完就可以安排房间了。时间旅行想去什么时候?”
他疲惫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浑浊的眼神终于有了微光。
“想回到我孩子出生那天。”
我听完一愣,忍不住好奇,问他:“那孩子是你的?”
“老弟,等我睡醒了,再告诉你吧。”
第二天上班时,别的客人告诉我,他房间里有音乐响动。声音并不大,也不算吵,只是有点奇怪。我走到他门前,听见那声音迷幻妖娆,鼓点飘忽不定,颇有异域情调。我本来打算敲门,后来转念一想,还是算了,我可不愿意再听他讲那些牛鬼蛇神的东西。
过了不知多久,音乐声停了。他走到酒店大堂,朝我要了一杯啤酒。
“我刚才在冥想。”他抿了一口酒,眼神闪出漆黑的亮光,“自由意志是万物的本源,主宰与造物都不可干涉。凡是造成自由意志泯灭的事情,都是错的。”
“够了,打住。”我直接打断他,“这五年你全用来琢磨这些了?”
“嘿嘿,我去过很多地方,这是我总结出来的,超越一切宗教和伦理。”他对我的不屑一顾毫不介意,反而显得很得意。
我为自己接了一杯啤酒,并不接话。
“我明天早上启程,可以吗?”
“你随时都能出发,只要你准备好了。”
他长出了一口气:“我无数次梦见那场面,如今终于能亲眼得见了。”说罢扭过头看我,“我确信,那孩子是我的,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见过孩子了?”
“见过。就在前不久。”他猛扎了一口酒,脸上的表情混沌而麻木。
“离开博卡拉后,我又去了几个地方,大概半年以后,回到北京。那时离我第一次游荡已经六年了。说来也怪,我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没在网上传过任何文章或照片,更没有为出书投稿的想法,但是,在路上遇到的朋友,好多人都说我已经成名了,至少在圈子里小有名气。回到北京大概一周后,开始有媒体找上门来。”
“那不是很好吗?混出名堂了。”
“好什么好?媒体人都是要下地狱的。你没看过伍迪·艾伦的一部电影吗?地狱的第七层到了,这层关押的是媒体人。噢抱歉,这层已经满员了。”
他学得惟妙惟肖,逗得我哈哈大笑。
“很有意思对不对?地狱里放着摇摆爵士乐,活脱一个大派对。他爸爸是犹太人,本来受到永恒的苦难,被宽恕后不想上天堂,只想去中国餐馆。想想看,如果在中国,地狱的最底层会关着什么人呢?”
“战争狂和民族主义者?”我试着回答。
“碰瓷的和道德绑架者,也许还有逃票的。”
我俩笑得不亦乐乎,碰了一杯。
“那趟回来,我只想去看看她。结果发现,她身边已经有人了。那人是个券商,西装笔挺的,看上去比我强多了。我像个跟踪狂一样,尾随他俩整整三天。她变得小鸟依人,注视他的时候,眼神里盈满了笑。那种感觉,我与她结婚后就再没见过。我真心觉得,那人比我更能给母子俩带来幸福生活。我就不要打扰了吧。”
“还是没有见着孩子?”
“那次没见着。各种人陆续找上门来,要把我包装成他们想要的模样。我不太喜欢上网,就去了趟书店,发现那段时间,净是这样被包装过的人,跟明星也没什么两样。书商也变成了人贩子。”
“都是混江湖的,总得有饭吃。”
“你倒是看得开。”他睨了我一眼,“只要不来打扰我,随便他们吧。”
“我在北京待着难受,于是赶紧上路。好像有一只手在后面推着我,一停下来,就要使劲浑身力气对付它。算下来,我已经在外面漂了将近十年了。你知道吗,我三十岁生日,是在火车上过的,那趟车空空荡荡,整座车厢也没几个人。我冲了一桶泡面,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旷野,特别想大声为自己唱生日歌,还幻想有个陌生人走过来,微笑着祝我生日快乐。”
我隐隐听见他一声叹息。
“从那一天过后,事情就变味了。我好像从没飞过出笼子,而是拼命撞开铁索,冲进了另一座笼子。以前很享受的事,如今变成了折磨。然后,我梦见那孩子,梦见他跌跌撞撞朝我走过来,梦见他哭笑,梦见他一边玩一边把东西打翻。直到梦见有一天,他变成我,变成一个我在路上遇到的陌生人——我突然惊醒了。我知道,冥冥中有什么东西将我推向归途,于是我回来,想亲眼看看那孩子。
我给她打电话。她约我在一家咖啡馆见面,我找了好久才找到。北京变化太大了,我在路上的时候方向感一流,回到这里却分不清东南西北。她穿得很漂亮,像动物园里的孔雀。两人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跟陌生人也没什么区别。聊了几句,我问她那个券商怎么样了。她说,早就把他踹了,那人控制欲太强,无论她做什么都束手缚脚,还是自己带着儿子舒服快活,更何况她现在富裕了,干嘛非得有个男人不可。
我跟她没什么可聊的,就谈起孩子。她挺自豪的,说孩子现在学习好,会弹钢琴,运动天赋也不差,就是有时候爱乱跑,害得她提心吊胆。母子俩出去逛街,她看上条裙子,转眼的工夫,孩子就跑到别处,自己玩去了,说过多少回也没用。现在的孩子普遍腼腆认生,不敢跟陌生人说话,他完全相反,逮着谁都想凑上去跟人搭讪。
我听完这话,浑身像雷劈了一样,因为我小时候就是那样,没少挨大人的骂。于是我问她,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她满脸嘲讽,说你现在倒关心起来了?可惜,我们娘俩已经不需要你了。
我后悔。如果当初没赌气,一走了之,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结局。我跟她说,想见孩子一面。她看了我半天,说要去接孩子放学,我可以和她一起去,但只能站在远处看,不能见面,更不能说话。等我亲眼看见那孩子的时候,我确信无疑。他长得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之后他沉寂许久,突然说:“我想现在出发,一刻也不想等了。”
19
他出发的时候,我看见门的另一边,一道几乎透明的绿光转瞬即逝。
三十。突然想起,过不了两年,我也要三十了。这数字就像个魔咒,不知道会不会像折磨他一样折磨我。二十五岁以前的一腔热血,换来的不过是一堆教训。曾经若即若离的人,如今也都成家,消失在茫茫人海。现在的生活,有时让我觉得安逸,有时却惶恐不安。
想太多也没用,大不了就像阿曼达一样,住在酒店里算了。
两个星期过后,他回到酒店。我很诧异,还以为他会一直留在那里。毕竟,只要他愿意,就可以一直待在那里,直到初入酒店那一天。
他向我们道谢,谢我们给他这样一个机会,能让他亲眼看见孩子出世。抱孩子的瞬间,他欣喜若狂,浑身发颤,激动得泪流满面。我问他为什么不干脆留在那里?他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样活过三十,说不定会更难受。
他走后,阿曼达从内堂款步而出。我问她为什么一直躲在里面,她说自己最讨厌那样的男人。她说:“这人浪迹天涯,满脑子都是虚无的东西,整天神神叨叨,没有一点正事可做,假装自己境界高超,无所不为。其实十年在路上,不过是逃了十年而已。”
真有这么糟糕吗?我问她。
那你觉得呢?阿曼达反问我。
我想,不过是个无家可归的人罢了。
大故事家系列短篇
「时间尽头的酒店」
分享时间旅行者的故事
第一季造纸街奇谈
造纸街16号|青年导演|飞女郎|假行僧
福祸相依|被逼婚的浪子|天才摄影家
族谱|朋克和尚|爱是永恒的摇滚乐
经作者授权发布,未经授权禁止转
作者:豆瓣ID离鹿
午夜写作者。旅游网站编辑。昔日的摇滚乐手,以及半吊子摄影狮。咖啡因重度依赖者,目前没有戒烟的打算。信奉自由意志,没有偶像崇拜。
长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