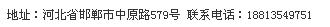许震这个春节,我在泪水中度过过年回家
许震
我的娘病了,大概在小年前的三天。
元旦期间,我请假回老家看的娘,送去了我年上半年给她的养老金,还看着让娘和大哥嫂吃下了梅河口公安局政委春良兄送给我的老山参。当时的娘,虽然是步履蹒跚,在大哥的小院里能走两三个来回,最多也就二十米的样子,但是精神还算矍铄,耳不聋,眼不花,看到大哥的鸡往她住的小西屋钻,她不时提醒我去撵。看到娘脸上红朴朴的,心里满是对大哥嫂的感激,一个劲地向大哥嫂道谢。
从老家回到北京的当天,我写了两首小诗,一首是《看娘》,一首是《好暖和哩》。《看娘》是写我的,《好暖和哩》是写娘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写完这两首诗的第二天,就病了。肚子拉得我天翻地覆,几乎所有的液体都顺着我的肛门往外倾泄,开始是两个小时去厕所一次,后来是一个小时一次,最后是半个小时一次。最严重的那一天,竟去厕所二十七次。一天之后,肛部的括约肌严重劳损,肌肉其间好像挤满了刀子,稍微一动,那刀子就会发挥作用,割裂我的神经,疼痛即刻传遍我的全身。我想哭,想叫,想笑。在几次控制不住之后,我叫过,我笑过,就是没有哭过,可能是年龄大的原因,已过四十奔五十的我,泪腺已如秋后的老井,水位很深了。夏天水桶随便一翻就汲满水的地方,现在却露出了斑斑驳驳的砖头、石块和几只无处逃生的青蛙,很难再汲上水来了。
平常时候,我一般一周给大哥打一次电话,询问下老娘的情况,说些感恩大哥嫂和鼓励大哥嫂赡养好老娘的话。小年前的一天,我心里空落落的,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想起有几天没有给大哥打电话,就拿起手机给大哥拨了电话。大哥说,娘病了,病了两三天了,他请村里的医生给娘打了针,病情明显好转,不用我挂念。我说,娘病了,医院,村里的医生行吗?别给耽搁了,毕竟老娘是快九十的人了。大哥一个劲地说,没事,没事。我当时心里不太高兴,你这老大也真是的,虽说关于老娘生病住院的费用白纸黑字写得清楚,由我们兄妹七人分担,但老娘住院的这两次所有的费用都是三哥和我拿的,你虽是老大,你没有拿一分钱,也没有人让你拿一分钱,你有什么好担心的?现在想来,大哥可能想到三哥和我挣钱都不容易,居家过日子,能省点就省点,医院医院。
小年后两天晚上八点多,大哥打来了电话,我的胸口突然紧了一下。娘在大哥家近两年半以来,大哥从没有主动给我打过电话,都是我不是一周一次,就是一周两次给他打电话。大哥打电话告诉我,娘病了,医院,心衰,肺部有积液。他还说,说好了,娘住院期间由兄妹几人一起照顾,都排好了班,我的班由他顶替。然后,大哥就匆匆挂了电话。我再打过电话去,大哥没有接。没有办法,我拨通了在我们兄弟们当中威信最高的三哥,三哥一听说我知道娘住院的事,马上火了:知道你在北京当警察出京不容易,说好了我们在聊城的这些人照顾,不让你知道!谁告诉你的?三哥的口气和声音不容我撒谎和犹豫,我说是大哥!
我的好兄弟姐妹,怕我因担心老娘而影响工作,主动承担了应当由我承担的那一部分。我是一名警察,更是我娘的儿子呀!
老娘住院的消息一袭进我的脑壳,我即刻进入了坐立不安的境地,谁在老娘病床前值班,我就给谁打电话,有时一天两个,有时一天三四个。大姐、大哥、二嫂、三哥、四哥和妹妹都告诉我,娘的病好多了。刚入院时,她老人家言语不清,四肢冰凉,两条腿已经不能弯曲,血糖23,高烧39度多,现在老人的体温37度左右,血糖降下来了,不到7,更重要的是两条腿已经有了些力量,自己能弯曲,多少自己能站住了。大年二十八,二嫂和四哥还帮老娘理了发、擦了身子。三哥告诉我,娘好得差不多了,各项指标稳定,计划初四就出院,要我别再挂心了。虽是哥姐嫂都说,不用我再担心娘的病情了,我还是放心不下,“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九十不留坐”,春节前的两天,我向单位领导说明我娘住院的情况,恳请他们批复我春节期间回老家看望一次老娘。单位领导十分同情和理解我,答应了我的要求。大年三十的晚上,我给在娘病床前值班的四哥打了电话,在向四哥道谢之后,四哥让我和娘通了电话。娘的声音洪亮,丝毫感觉不到在住院的样子,问候了我、我的妻子和孩子。老娘说,不要我挂着她,她好了。
据说,大年初一上午,娘的儿孙、重孙们等几十口子都向她拜了年,她一直笑呵呵的。可不知道什么原因,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她老人家就高烧起来,一直烧到39度多。初二的上午,我妻子催我,这一天多没有给娘打电话了,看看老娘怎么样了,是不是初四真的出院?我说,应当没有大问题,三十晚上,咱俩不是都和老人磕头拜年了,听那声音和平时没有生病一样,不会有问题。妻子说,还是打电话问一下吧。我躺在客厅的沙发上说,我的身体有些不舒服,有些胸闷难受,你打吧。妻子用我的手机给正在值班的大姐打了电话。大姐说,娘发烧了,39度多,医生用了所有降温的办法,就是降不下来。她老人家一直张着嘴,喘不过气来,脸憋得通红。妻子一听说我的老娘快一天了高烧不退,就着急了。医院工作的同学赵海燕的电话,医院进修过的骨科主任王海领的电话。两个电话打出后,都没有接听。越找谁谁越不在,一个电话打不通,另一个电话通常也打不通,这似乎是无法用今天的科学解释的一个规律。没有办法的妻子就在医疗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