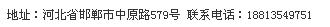郑晓红用麦粒喂养石磨
在五千年遗址上酿浊酒一瓮郑晓红之一用麦粒喂养石磨那盘石磨卧在南佐遗址院子一棵老槐树斑驳的阴影中,经年的灰黑色菌衣隐隐泛起潮腥的霉气,老树漏下的光斑在磨盘上水纹般跳动,新苔悄然攀上,时而隆起或凹陷,收拢又打开,仿佛金色斑点的舞伴。不管阳光怎样逗引,任老树将断枝投在它身上,一只善意的布谷鸟忍不住啄断一串种实掷下来,石磨僵卧依旧。谁都看得出,它的梦境是一片死寂的荒原。它在这大塬上存在了一百年还要多吧,可比起塌窑里那盘汉代老磨,它青春的芽儿才发,正茁壮的年纪,哪里敢言老?只是,磨心太久不转,锈住了吧,活力被时间摁了封印,记忆跌入深渊。那由磨脐发出的吱扭扭的声音,绕着磨盘轮回了几生几世的踢踢踏踏的足音,还有自磨眼流入磨膛的粮食的沙沙声,与它一同掉进深远的黑暗,仿佛它一时任性拔脚去了天涯,至今没能找见返程的路。曾经有只路过的鹪鹩落在它身上,脚爪纤细,在磨扇上挠几下,丢下一串鸣声玎玲,扑棱棱振翅而飞,宛然一道倏忽而去的闪光。它却被挠醒,一阵颤栗。一个如火漫过的黄昏里,它的记忆出了鞘,借日光的刃相互擦亮。子午岭深处一处崖壁下,它第一次感受到与阳光抚摸迥异的另一种温度。一只粗糙的手掌覆过来,上下摩挲着它,茧皮的坚硬摩擦着它的坚硬,在沙沙的厮摩中,一股异样的温暖浸进它冰凉的石心,它听见一个苍老沙哑的嗓音说道,多好的一块青石啊!老人选中了这块荒石,作为他石匠生涯的最后一件收关石磨。他再也不想顶着给主家交货的压力与时间较劲了。定好圆心,第一锤敲下去,他就下意识放缓了节奏,一锤一幕,一幕一锤,影像交互闪动,他一生雕凿过的柱础、门墩、拴马桩、石磨、碌碡、石盆、石臼一样样布排开去,又幻化成滚滚的麦粒、玉米粒、豆粒、高粱粒向他手底的磨盘雏形涌回来。他头一回察觉,自己的一生竟是结实而壮阔的,身后的土地与人家里,都留有一样被他的汗水浇灌过的石器,物件留下,仿佛不是因为生计的交易,而是为着体恤他丢掉的那几分气力。石屑纷飞,上下两盘磨扇逐渐成型,上盘负起旋转碾磨的重任,比下盘更厚。而后,老石匠稳稳神,开磨眼。不过是开个孔洞而已,可他凝神聚心,他觉得,要开的是石磨与一个家族息息相通的心眼。铺齿是最讲究的一道工序。人都说,石磨里头有八卦,指的就是这个。上下磨扇的结合面,要凿出交错的八块齿岭,转动起来,俨然旋转的八卦图。老石匠不懂卦象,不会为这份神秘去精雕细琢,他只知道,齿岭是石磨的牙口,每一道都得凿成外高内低,让磨扇在相互咬合中,将粮食颗粒磨碎并沿齿隙汩汩而出。石磨成型了,他刨去石屑,吹去浮尘,双手覆在磨顶上,枯坐良久。錾这最后一件就收关啦!他舍不下这锤,这钻,这荒石在手底变形的快慰。叮叮当当,又敲打起来。磨顶是“天圆”,他要凿出“地方”,一方只有四角,他要凿出两方相套,指向人间八方。最后,他以磨眼为心,凿出一朵宝相花,将吉祥美满的祈愿送给天地人间,也留给自己。这是这块塬上最美的一盘石磨。老石匠心满意足,了无遗憾,甩着胳膊远去,佝偻进他自己的时光里。当第一筛麦粒注入磨眼,石磨顿时从懵懂中醒来,心窍洞开。粮食颗粒痒酥酥流进磨膛,犹如水瀑跌入深潭,而后依着地势泻向四面八方。磨齿的咬合与麦粒粉碎的声音相互消解,变得包容绵长。它愿意转动,被那头蒙了眼的驴拉着,一圈又一圈。它听着驴子踢踏的蹄音与粗重的呼息,驴子听着磨盘下挤压、磨碎的声音,它俩借着声音互通款曲。它学会了像驴子那样喘息,由磨眼里,由磨齿里。它觉得,粮食就是它的草料,它像驴子一样被喂养,也是一匹能够不停转动的活物。齿岭间流泻而出的粉末,像是信使,让人间与石磨达成了相互补偿相互托付的生命契约。它活物般的日子过了多久?记不清了。它依稀记得,那头驴子老了,皮松肉耷,垂着头,嘴角淌沫,走着走着就停下来。磨棒只好卸下来,套在一匹骡子身上。骡子本来就不年轻,走的沉重拖沓,呼哧呼哧喷着热气。不使唤牲口时,家里的女人和孩子就来推着,它陪着两个女人老成了婆婆,四个小囡转啊转的嫁了人,六个楞头小子娶了媳妇。它不老,它天天渴望粮食,天天渴望转动,錾它的老石匠,仿佛把自己几辈子的气力都留给了它。它以为它能地老天荒地活着。可是,那份生命契约被人类单方撕毁了。在村头的一间新磨坊里,一架电磨仰天长啸,它不明就里,一跟头跌进死寂的梦里,梦境里横亘着崖壁下那块荒石——它未曾注入生命的前身。一个苍老沙哑的声音隐隐传来:多好的一块青石啊!在南佐这个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上,石磨想以它一百多年的光景倚个老卖个老,实在拿不出手。它的祖先,五千年前的石杵石臼就卧在这院子里……它们都是活在慢时光里的物件,万物活着的细节都镶在静水深流般的慢镜头里,年前的先民可以花一两年的时间去打磨一枚石斧,年前的老石匠可以耐下一两个月的性子去錾一盘雕花的石磨……可时光已然推进到一个疯狂提速的时代,批量的家禽,批量的生猪,批量的面粉与食用油,批量的粮食种子,批量的新农村,批量的古城、古街、栈道、与亭台楼阁,批量的门店招牌,批量的春联与年画,批量的香包、灯笼和剪纸,批量的绣花鞋垫、砖雕、木雕,批量的桌椅柜子,批量的妆容与饰物,批量的网红脸,批量的噱头、段子、广场舞姿,批量的群发祝福……当然,还有批量的机打石磨……飞奔的脚步让身边的风景一闪而过。我们只是扭了扭头,一朵花就熄灭了。个性的湮灭注定了文化的单薄。在被篡改与扰乱的自然秩序中,我们只是微微叹息一声,依旧顺应着人潮向前走。我们的肉身终会腐败消融于黄土,可经我们之手创造出来的器物却会留存下来。难以想象,成百上千年后,被机器批量生产出来的器物,将以怎样的文化面孔闪耀在后人的端详中呢?南佐遗址院子里的任何一个器物都是经得起凝视的。单单一样石狮子,就活出了几十种面目神情和蹲踞姿态,每一个慢时光里的匠人都赋予它们自己对天地的观察与理解,雕凿的石狮子可以是呆萌的,委屈的,沉思的,恼怒的,淡定的,禅修的,凶悍的,顽皮的,脑袋可以是双面的、四方四正的,甚至狗面猴面的……当一狮呈现千面时,那是一个想象力与创造力多么嚣张、狂野、没有边界、张牙舞爪的艺术童真时代啊。匠人们早已化为尘灰,可他们的个性、时代渗透在他们身上的共性都借着石兽得以保存,后人端详每一尊器物,同时端详了线条、刀工、造型里潜藏的历史痕迹。院子里的几十面磨扇,同样是经得起长久凝视的。所以,当一位老妇人走到老槐树下,看到那盘枯枝横斜、菌衣斑驳、苔藓流动的石磨时,她停下来惊叹一声,多好的一盘石磨呀。她把手掌覆盖上去,仿佛看到了围着石磨吱扭扭盘旋的她的少女乃至少妇时光。石磨感到了手掌的温度,磨心一热,醒了过来。它像迷途才返的孩子,太大的委屈要用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