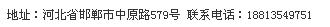我的左眼
眼科手术室是一个长长的回廊
护工把我推到了十号手术室门前,低下头,俯在我的耳边轻轻地说:“就在这里等着。“
沪上四月末的天气有些冷。
我是那天最后的一台手术,手术室走廊的地面是一个一个的方格子,涂着难看的绿白色,走廊的尽头有一扇巨大的窗,太阳已经西斜了,是那种土黄色。
手术室厚重的门开了,一双白细的腿走出来,甚至看不到腿毛,我以为是一位女性,那人长长地叹了口气,“吃力来”,我抬起头努力地对他笑了笑,“辛苦”。
那人长着一张女人般精致的脸,手也纤巧细长,相邻的楼上有人不知道是在开还是在关闭窗户,一道光反射过来,刺痛了我的眼睛。
他走过我的身旁,一股浓重的消毒水的味道。
想起了虹。
明乾寺在县城外一个高高的土岗上,有二十多间房,和尚被赶走了,成了城关镇小学。大雄宝殿就是老师办公的地方。每当去请教老师都要爬上那十几级高高的青砖台阶。寺庙的后面有一座建于隋朝的文峰塔,砖结构楼阁建筑,每层楼阁均为六角,共13层,是我们登高玩耍的好去处。塔顶的砖缝里钻出一棵盘根错节的石榴树,秋天到的时候我们会比赛谁能把石榴树顶端的石榴采下来,那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我每天都会仰望那阳光下的石榴树。
土岗下面是一条宽约三十几米的河,枯水的季节,河岸的两边长满了青青的芦苇,河水荡漾。
虹的父亲就在城关镇做革委会主任,他是从省城下来接受改造的,虹兄妹俩随着父亲来到这个地方,成了插班生。
虹兄妹俩就住在大雄宝殿旁边的偏房里。
虹穿着一双搭绊的布鞋,雨过天晴,她都会洗刷了晾晒在高高的台阶上,鞋白色的衬里在阳光下耀眼。我总在想怎么会那样的白。虹总是不带一丝的尘。虹的皮肤是麦粒色,有一双大大的眼,嘴唇也与众不同,是那种暗红。
有一年秋天,一阵暴风骤雨把学校那棵挂着铜钟的老槐树的枝丫吹断了,地上厚厚的一层槐花,钟碎了。教导处的甄老师用刀把树皮剥下,用毛体刻了大大的“光明”两个字,引来了师生们的围观,这块树皮做的匾就挂在了学校校办工厂的门口,说是校办工厂,其实就是一间矮矮的平房,生产着师生们用的蓝墨水,红墨水和黑墨水。墨水盒上的标贴后来也换上了这两个字“光明”。我们盼着很快把墨水用完,这些墨水瓶子被装上了各种的油就成了我们的油灯,每天的晚自习这些灯发出昏黄的光冒着浓烟直冲屋顶,一节晚自习下来我们的鼻孔就成了黑色。虹就坐在我的前排,两条粗大的辫子时不时随着她身体的移动扫过我的油灯,不是翻我一课桌的油,就是燃着了她的辫子。我每天读着散发着柴油味道的书,看着她又粗又黑的辫子。
那是两个人的作业本挨着都感到幸福的纯情。
虹的哥哥耀,大我两岁,按照他爸爸的意思,要照顾妹妹就和我们同班了,耀胆小,这座古庙改成的学校里除了两个值班的老师守夜,就只剩下耀和虹兄妹俩了。耀总是尿床,常常夜里惊醒,第二天会把褥子晾出来。虹就要我晚上陪耀一起睡。早上我和耀起来,虹已热好了馒头,装好了稀饭,馒头是她爸爸从公社的食堂买回来的,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用小麦做的馒头,我会带些奶奶做的酱夹在馒头里吃。
有时候周末虹的妈妈会从省城过来看他们,我们三个小孩儿就到大雄宝殿后面的房间里睡,睡醒了起夜推开门有些亮,虹的爸爸妈妈住的房间里还透着灯光,能听到他们的嬉笑声,窗台上有个人踩在椅子上踮着脚向里窥探,我揉了揉眼看清了是我们的校长,我悄悄地回到屋内,屏住了呼吸,生怕他发现我。
这座庙里每天都响起朗朗的读书声。
夏天,学校边上的河涨水了,河水湍急。中午,我会喊上班里几个同学下去游泳……奶奶每天都会在我的背上用毛笔画上一个圈,放学后以那个圈是否存在查验我下没下过水。这难不倒我,游好泳让同学再画上就是。
当我湿着身子回到教室,虹嗔怒的瞪着眼看我。
于是,我再下水的时候,刚跳下河里扎几个猛子,奶奶就适时的拿着竹竿出现在河岸上,喊着我的小名,把躲在芦苇丛中的我揪出来交给班主任。
班主任姓苗,很瘦,扭着我的耳朵让我光脚站在太阳底下声嘶力竭的呵斥我,我从他的肺气嗅到一种死亡的味道,那是偶尔经过县里的屠宰场空气中飘过的气息。我不由自主的大哭起来,如丧考妣。
那晚上开始我梦中梦到铺天盖地的蛇,各种的蛇。我坐在地上,试图一条一条的把它们摆放整齐。
这样的梦一直挥之不去。
到冬天下大雪那天,苗老师没来学校。
他死了。
学校里组织给他送殡,我和同学抬了花圈站在他的墓穴前,那是头天有人挖好的,那天四周都是灰色的白,只有墓穴的四壁没有被雪覆盖,露出黄色。看棺材晃了几晃落在坑底,老师们匆匆忙忙的用铁锹铲土填上。那土混合着雪。同学们和送殡的人一起哀嚎。我没哭,夏天里哭过了。我把一只脚从棉鞋里拿出来,踩在雪地上,一股莫名的温暖。
我想起了那天光脚站在阳光下滚烫的土地上被苗老师揪着耳朵。
护士过来核对了我的名字,我被抬到了手术台上。主刀的教授来了,护士长说:“主任,院办要让你把责任书签了。”教授离开我,“TMD,一年要做台手术,我这是卖身!不签!“又回到我的头边,摁住我的头让我别动,护士长又说:“主任,这个病人术前有张单子还没签,先签了才能做手术。”教授又离开我,过了五六分钟回来。
忽然有一天,虹和耀都不见了,听老师说虹的爸爸去了省城,也把虹和耀带走了。我有些失落,课桌里有一个铅笔盒,里面躺着一杆英雄的金币,我知道那是虹留给我的。那年,那棵老槐树不知道为什么没开花。那个铜钟后来修好了,挂在了另一根枝丫上,声音远不如以前清脆,有些沉闷。
过几年我考进了省城的一所重点中学。有一天上完早自习觉得眼睛疼,医院。医生诊断说是虹膜睫状体炎,打了封闭,医院,雪很大,碰到了耀。耀骑着一辆警用三轮摩托,他已经是一名警察了。我们惊诧于这样的相遇,他问了我情况,就让我坐上车,载我回家。耀的爸爸已经官复原职,住在省府的大院里,这个大院应该是一座很老的官府,有几进几出。我们七拐八拐才走到耀的家。走进一个暗红色的小门,门上的油漆不知刷过多少遍,虹就坐在正屋的走廊那儿,晒着太阳,在大声地朗读着高尔基的《海燕》。看到我进来,只一笑,仿佛几年的分别只是昨天。她已经在一个师范学校读播音专业了,放寒假在家。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教授回到手术台前,划开了我的左眼,眼前一片殷红,我再也看不见了。教授说:“疼么?”然后吩咐护士再打点利多卡因。眼前是混沌的黄色。
当我的紫葡萄酒化作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凝望着血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虹把外屋的煤炉封好又坐上一壶水,走进来。被子白天晒过,有阳光的味道,那是她的闺房,她用手抚摸着我的脸,“疼么?”我摇摇头,“我妈说你心硬,我不管”。
教授说这个搞摄影的眼睛真硬,他摁紧了我的头。
耀学会了抽烟,每天找些邓丽君的歌来放,他医院的眼科做护士。下了班就过来吃饭,帮我打针,春节过了,虹开学了,到另外一个城市。
脚特别冷,身子下的汗水把衣服都浸湿了。教授说:“不要急,快好了。”我想说我很冷。
我穿上了军装。
走的前夜,用自行车载了虹到郊外的伊逊河边上。
月亮是橘红色的,在天边的地上向上跳了两下就挂在半空了,慢慢地变的银白。
伊逊河水流很急,靠岸边长着一丛丛连绵的芦苇,被水冲的仿佛站不住脚,前俯后仰。芦苇的叶子摩擦着,散发出青青的香。
月光照在河面上。
有一两根独立生长着的芦苇,顺着水流倒下再努力地挣扎着站起,站起和倒下的瞬间把月光击打的粉碎,像碎了一地的镜子。
河堤上种了些黄豆,仅留下很窄的路,我一手推着车子,一手拉着虹。黄豆的枝杆不断的缠到车轮的钢丝里。四周不时有蟋蟀扯着嗓子的叫,我们走过便嘎然而止。
虹攥紧了我的手:“我们就在这儿坐吧”。
我看着她,在月光下。
沉寂了一会儿的蟋蟀终于忍不住,先是试探的低鸣两声,接着就是放声的歌唱,引来周围此起彼伏的共鸣。
那儿的夜本来就是它们的世界。
虹躺在我的臂腕里,我们能听到彼此的呼吸。
“带我一起走吧”,虹说。
我俯下头,她眼里满满的晶莹,映着月光。
我吻她温软的唇,唇边是湿湿的咸。
那时候河里还有鱼,鱼儿不时的跃出水面,在半空挺直了身体,向上,向上。
你是想飞吗?
它的世界又拼命的把它拉回去,鱼儿只好掉头往下,在入水的一霎那竭力的调整着进入的角度,唯恐伤了自己。
人又何尝不是这样。
虹的肌肤如缎。
虹来送我,从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挤过来,手里举着个用过的罐头瓶子,瓶子里是两条水泡眼的小金鱼。我伸手去接,被身后的人推挤了下,失手掉地上,脚下是干的泥土,水在地上马上消失了,只留下些许的痕迹,金鱼尾巴拍打了几下就再也不动。虹蹲在地上,试图用手捧起来却被碎的玻璃扎破了手。我掏出她送我的白手帕,把她的手包了起来。
她用双臂环着我的脖子,哭。
我轻轻的拍着她的背,安慰着她。
眼光越过她的肩,我看到了那个给我左眼的人,只一闪,再不见。
虹还在哭,她的泪水湿了我的半边脸,有些蜇的痛。
地上的金鱼已经被人踩到了尘土里。
——那是我们无法安置的爱情的归宿吗?
南方战事紧,我随部队在内蒙驻训已经几个月了。
一个叫大阳坡的地方,是一块绿洲,不远就是望不到边际的沙漠。
没有虹的信。
……
我躺在村头的高坡上,看将要彩霞满天的夕阳。
——常常会出现彩虹。
下午刚下了一场雨,草地上还有些潮湿。
连里的通信员找到我,递给我一封信。
是虹的。
没有地址,看邮戳是两个月前的,仍然是她读书的城市。
信封里只有那方白手帕!
有血的地方绣了几朵精致的梅花,那种暗红。
我把手帕蒙在脸上,寻找着虹的气息,淡淡的皂香。
泪水慢慢地溢出,直到,直到觉得手帕有些凉。
起风了。
那个季节草原上的马兰花正在盛开。
我在一丛马兰花上系住手帕的四角,看风把手帕吹的撑起,像一张大海里船上张起的帆,手帕一点一点不舍的升起,挣脱了马兰花。
它能飘多远呢?
——在那大漠深处。
不能承诺下次何时
你热情的手你的吻
你的温柔
将你的一切我定不会忘记
请不要望着我的背影
强忍着眼泪的分手
Lastsongforyou
Lastsongforyou
将你的一切我定不会忘记
我不会望着你的背影而走
我们有真实的历史吗?
一场风轻云淡的邂逅。
教授拍拍我,手术结束了。换了人,他给我缝线,我的左眼看出去是红色的。
会好吗?
我想着。
海水是咸的么?
我想着自己一夜白了发,坠入海的深渊。
白发在水中摇曳,我想起了那晚的芦苇和跃起水面的鱼。
那天是我的生日,后来我知道给我左眼的人也在那天走了。生命中就是有无数种那样的巧合。他喊着我的名字。
“有我的饭吃么?“他盯着锅里翻滚的鱼,我坚决地摇了摇头,我只看到他的喉结抽搐了几下,他试图用被香烟熏的焦黄的手触碰我,又颓然地放下,拉开门走了。他应该给我送来治眼睛的费用,可是没有。我再也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那个给我左眼的人。
血气已和,荣对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
我知道他临终的时候一定会想到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起那晚锅里沸腾的鱼。
上帝总是站在高高的山岗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Godsaid,lettherebelight,andtherewaslight.
白癜风康复成果展如何确定白癜风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