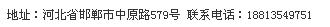当代电影论周星驰的残酷喜剧
学术
视野
作者:陈奇佳陈小可
责任编辑:刘桂清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来源:《当代电影》年第12期
一
自20世纪90年代初崛起以来,周星驰已成为华语喜剧电影的一面旗帜。不过,如何界定其作品的艺术内涵、分析其艺术特点一直以来还是一个问题。大众媒体坚持用“无厘头”(1)来概括周星驰作品的“精髓”,但熟悉周星驰的人们早就感觉到,他的电影并不总是那么好笑,那些笑点也绝非空洞的为笑而笑。一些研究者尽管也套用“无厘头”的说法来评论周氏喜剧,但他们笔下的“无厘头”多有现实的或艺术上的针对性,有着明确意指。按照此类说法,“无厘头”已成为“有厘头”。(2)
“无厘头”毕竟是周星驰崛起之初香港媒体对他艺术风格的一种不甚严谨的概括,并且,似乎还有着一种对现实社会政治讽喻的意味。(3)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在顶着最初的“无厘头”标签之后,周星驰又拍摄了许多作品:早期作品中相对单纯的为笑而笑的场景已急剧减少;而艺术形式上则显得越来越考究。我们认为,自年与杜琪峰合作《审死官》开始,周星驰对自己的电影艺术风格有了较为自觉自为的探索。这种探索在年的《大话西游》中,特征已相当明确,并一直贯穿到了其后的《食神》《国产凌凌漆》《喜剧之王》《少林足球》《功夫》《长江7号》《西游·降魔篇》《美人鱼》等一系列作品中。总体来说,周星驰在这些作品中似乎都在追求一种“残酷”与“喜剧”的平衡。所谓“残酷”是指这些作品的故事主题一般都包含着某种残酷意念,体现出他对我们生存的世界情况偏向于阴冷凄惨的理解;而“喜剧”则是指他会用大团圆的俗套故事和狂欢化的搞笑场景将这些残酷的意念包裹起来,甚至直接把它们当作笑料,让思想的锋芒显得不那么突兀伤人,但有心者自然能从其中品咂出别样的滋味。相当程度上,正因为他拥有这份对残酷的坚持,他的作品才脱离了香港一般同类型喜剧作品的窠臼而显得较为意味深长。当然,“残酷”与“喜剧”之间的平衡殊非易事,如果残酷这一面显露太过,作品就难以吸引人,对世残酷性的深度谛视亦非周星驰所长(如《长江7号》),但如果过于突出喜剧性的一面,则又不免落于商业的俗套和油滑。相对来说,《喜剧之王》《美人鱼》是“残酷喜剧”在艺术上表现得较为圆融的两部作品。
没有疑问,本文所讨论的“残酷喜剧”的概念得到过阿尔托“残酷戏剧”观的启发。阿尔托曾经指出:
残酷一词……并不意味着暴虐狂及精神反常,并不意味着畸形的感情及不健康的态度……我决不是指作为恶习的残酷或作为恶念萌生的残酷,因为这样的残酷正如受感染的肉体上长出病态赘疣一样,必须通过流血才能表达出来。恰恰相反,我指的是一种超脱的、纯洁的感情,一种真正的精神活动,而这种活动是对生活本身的动作的仿制。……不论偶然事件是多么盲目地严峻,生活不能不进行,否则就不称其为生活了。这种严峻,这种无视严峻,并且在酷刑及践踏中进行的生活,这种铁面无情的、纯洁的感情,其本身就是残酷。(4)
他因此进而说道:“我们迫切需要这样一种戏剧:它不会过时,它在我们身上引起深刻的回响,它控制了时间的不稳定性。……凡是起作用的就是残酷。戏剧应该按照这个极端作用的观念来更新自己。”(5)我们所说的“残酷”,基本上就是依托阿尔托的这些核心观念来展开。诚然,周星驰未必知晓阿尔托的理论,(6)但这并不妨碍他可能自发地产生一些与阿尔托近似的艺术意趣或见解,这是不必多言的。
以下我们主要从暴力世界、底层生活、“真爱有敌”三个方面简要评述周星驰式“残酷喜剧”的基本构成要素。这三方面是周星驰电影较重要、亦是最具文化影响力的内容构成部分。
二
周星驰的电影虽然都号称“喜剧”,但仔细分析其作品所描绘的世界基本情况,却没有多少让人和谐平静、心情愉悦的内容可言。从《审死官》开始,他的几乎全部的作品(包括主演、执导),其故事背景几乎都笼罩在暴力的阴影中,暴力因子充斥在大量的故事场景中。
当然,在大多数的场合,周星驰会调动一系列局部的叙事技巧(如误会、巧合、戏仿、夸张、降格等等),使得故事中的暴力因素显得古怪且笨拙,本身就成了一个笑点。如《喜剧之王》混黑社会的洪爷在扯谈话剧《雷雨》的时候,胡说什么《雷雨》故事的真谛就是讲义气,讲义气又略等于混黑社会砍人,“砍人”具体又分“砍”与“捅”两种。《国产凌凌漆》里袁咏仪饰演的李香琴糊里糊涂地使用凌凌漆的“古灵精怪枪”,几次试图打中凌凌漆,却每每误伤自己。《美人鱼》中美人鱼珊珊潜入富商刘轩的住处行刺,几次三番弄巧成拙,行刺不成反倒殃及自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些剧情中,周星驰可谓是调戏了暴力,在暴力伤害的痛苦未足够刺激观众之前,他就用巧合等戏剧手法建立起搞笑的幻觉,转移观众的注意力。
但暴力毕竟是暴力,其残酷性在很多时候并无法被喜剧元素转移或稀释。《美人鱼》更把他之于暴力、血腥场景的偏爱直接表达了出来。影片大概用了长达七分钟来表现故事中的兰总带人捕杀美人鱼的场景。影片中,机关枪扫射下的水域瞬时染为猩红色,美人鱼们被迫跃出水面,纷纷被擒获或屠戮,镜头给尖利的机关枪箭头以特写,金属在昏暗的环境中闪出白光,寒意逼人。在这几分钟里,甚至人们会忘记他们正在观看一部传统的周氏喜剧,几乎没有人为屠杀快意大笑,因为那场面显得太真实而残酷。机关枪扫射的同时,这部电影也在观众那里投射下炮弹,令人猝不及防地感同身受。而在《国产凌凌漆》中,暴力带来的残酷虽不似《美人鱼》那么震慑,却也足以让人心悸。故事中的凌凌漆在商场里遇到几个劫匪老乡,这几个劫匪在被警察追捕的过程中顺手劫持了一个小男孩作人质,小男孩的父亲苦苦哀求劫匪放了儿子,劫匪却恼羞成怒地当着小男孩的面一枪打死了父亲。这个场景在影片中是突兀而来的,没有任何附加的幽默搞笑。暴力因子在这里不是以艺术化的渲染出现,而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残暴:毁灭美好事物的本性与冲动,这样的情节设置比任何黑帮斗殴中的血腥都更具有令人哀痛和同情的力量。
围绕着暴力,周星驰的作品还展现了它的诸多面相,如情欲、欺诈、霸道、压抑、啰嗦(《大话西游》中的唐僧可谓是纯粹“话痨”暴力之典型)、义气等等,其中,最能彰显他的残酷意念的,是他对“吃人”意象的偏爱。他的作品经常有直接的吃人场景。如在《九品芝麻官》中,故事主人公包龙星等人参加戚家痨病少爷的婚礼,少爷在婚礼上不停地咳嗽,最后捂住嘴一伸手,吐出了一块肝。包龙星好奇地问:“喂!这是什么东西?(手中拿着肝)是块肝呀!吃火锅了?老兄。”继而包龙星顺手把肝塞进师爷嘴巴,师爷饶有滋味地吃下了那块肝。这个情节的设置绝非仅仅为恶搞而恶搞,师爷吃下去的“肝”也不只是火锅配菜,而是“吃人”意象的转化。又比如《西游·降魔篇》里被鱼妖一口咬下的小女孩,炉子里的人肉烧烤,《美人鱼》里被活吃的章鱼,都是残酷“吃人”的隐喻和转化,这些场景触目惊心。
当然,周星驰绝不是为暴力而暴力,其表现“吃人”意象也不单纯是为了引发恐怖效果。否则,他的作品就跟《人肉叉烧包》之类没什么区别了。“有人认为残酷就是血腥的严酷,就是毫无意义地、漠然地制造肉体痛苦,这种理解是错误的。”(7)周星驰的影片中凝视各种人类之间的暴力行径,多半含着一种善良意愿:人跟人之间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他大概在《济公》中首次直面叩问了这个问题。(8)故事中的假道士招摇撞骗,说城里瘟疫四起需要活人献祭,街上的百姓问去哪里找这种送死的人,一个上了点年纪的大妈插嘴“怡香院里多的是”,于是众人群结赶往怡香院。于是“九世野鸡”小玉就被选作祭品绑到了火堆上(这其实是一个转喻版的吃人故事)。故事中的众人其实并不知道烧死小玉和解除瘟疫之间的关联,可是在一个哪怕是极其脆弱的力量驱动下,人们就会给自己找出堂而皇之的杀人理由来毁灭另一个人。借故事主人公之口,周星驰感叹人情之自私冷漠乃是人世间祸害动荡的根源。
↑《西游降魔篇》
→《美人鱼》
不过,人的自私自利乃是天性使然,如何让人必然地超越这种天性中的暴力因子呢?周星驰看到了病症,却提不出什么解决之道,这也导致了他所执导的作品在结构上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弱点:情节设定有创意,矛盾冲突很凌厉,故事笑点有内涵,但矛盾的解决很草率,近似于“神仙打救”,如《食神》中观音降世、《喜剧之王》中结尾突然出现的贺岁场景、《功夫》中阿星突然悟到“如来神掌”绝技等等均属此类。不过其近作《美人鱼》预示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似有突破。电影里面出现过的台词“假如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分钟,假如地球连一滴干净的水、一口干净的空气都没有,你最想干吗”即是故事主题。这个看似平常的环保理念却通过整个故事的残酷性得到了升华。故事中美人鱼的处境颇可视作人类未来生活处境的预言。人们不难看出:美人鱼栖居的那条破船所在之处环境曾经也热闹一时,零星的霓虹和“海鲜酒家”的招牌都昭示着这里曾经的繁华,然而一切热闹终将消散,到头来难免沦落为生存最后的避难所。美人鱼介乎人、鱼之间,美人鱼的避难所也介乎人类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那艘破船不仅仅是美人鱼们的生活环境,也是人类在自然中可能面临的生存境况——如果不注意保护环境的话,可能连一艘破船那样的栖息地都会不复存在,人类只能走向灭亡。这样就能够得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推论:自私自利的人们为了实现其自私自利、凡事功利当头的目的,倒有必要友爱团结起来,不然就只能自取灭亡。故事中的刘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当然还有一些爱情因素的推动),完成了人格的巨大蜕变,从一个极端自私冷漠、唯利是图、狂妄自大的人变成了一个有原则、讲公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