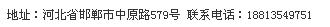2007,似水流年的每一天
一转眼就到了年底,从前的日子不紧不慢,每一年都是不多不少天。十年来,我坚持在年底的那一天写一篇《似水流年》,翻了翻,都还在,有无病呻吟,也有叙事感怀,从今天开始到三十一号,天天似水流年。
回望昨天,方知现在。
(年夏天的我)
,似水流年的每一天
《恋曲》是罗大佑的,《我的》是艾敬的,奥运是全国乃至世界人民的。
,似水流年的每一天,是我的。
多年前,王二关于似水流年做了解释,大致是说,似水流年是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只有这个东西,才真正归自己所有。其余的一切,都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转眼间就跑到似水流年里去了。
王二写完这些东西,也中了邪似的躺进河底,终日与普鲁斯特为伴,眼看着潺潺流水,粼粼流光,落叶,浮木,空玻璃瓶,一样一样从自己身上流过去。
子曾经也在川上曰过:逝者如斯夫!斯,就是逝去的流水,简单点说,就是似水流年。
如今,他们都躺在河底,而我尚在岸上流连,所以才能信手将这段解释贴在前面,只当作是自己的似水流年。
第一季死亡
流年似水,有的事情一下子就过去了,有的事情很久也过不去。
当时的寒冷依然刺骨,但是,不会有谁把肃杀的寒冷和无可挽回的死亡那么逼近地联系在一起。
隆冬,黑夜,穿云破雾,从北京到成都。
父亲刚坐上床,棉袄在身上,绒线帽在头上,见到女儿,老泪开始婆娑:爸爸不长了。忍住哽咽,抱着父亲,女儿说:不会的,不会的,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那时的父亲还能行走,几天后,双腿开始颤颤巍巍,又几天后,思维开始迷迷糊糊,再几天后,脚背开始浮肿,声音开始无力,
那天早上,父亲说,把他的头朝向西方。
下午的时候,气息微弱的父亲再也没有睁开过双眼。
晚上9点,父亲不再心跳呼吸,他勉力睁开的左眼在母亲的手掌下再次合拢,想要表达的嘴唇,嗫嚅着却永远不能闭上,那双被光荣磨损过的双手在声嘶力竭的挽留中渐渐变硬,将世界慢慢松开。
几天后,父亲完整的躯体从通红的炉腔中出来,鼓风机吹开,一堆白骨不过三尺。
一个潮湿的日子,父亲被埋进潮湿的土地。
有一些时候,会思念,记忆开始的时候,父亲已近中年,总是凹陷的脸颊,总是瘦削的身材,总是在昏黄的白炽灯下写着什么,有时候,还能听到屋子里传来的几声咳嗽声,分不清是父亲的还是自己的。
有一些时候,会绝望,伸出手,再也握不到温暖的手心,再也听不到慈爱的询问,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就不再回来,没有灵魂,没有来世,没有生者与死者的对话。
有一些时候,会分裂,会困惑,会有来生永不再来,此生不过如此的慨叹,这荒诞不稽的岁月,生亦何欢,死亦何苦?
肝肠已经寸断,柔弱已经不堪,我们这些不得不继续忍受煎熬的人,还要继续忍受;
放不下与生俱来的重负,而维系生命的光芒却如此易断,死亡的阴霾如沉郁阴云,挥之不去,我好像一直在等待,等待所有熟悉的面孔被埋进地底,直到自己彻底孤单,不再被亲人烦扰,不再为尘世所累,直到我们终于抽身离去。
第二季心痛
流年似水,有的人很快就忘记了,有的人从来都不曾想起。
回京的时候,护城河冻结的冰面又化成了静默不语的水,京城内外又开始年复一年的杨絮飘飘,飘进眼睛,飘进窗台,飘进每一缕呼吸里。
杨絮飘飘,飘进了春夏之交,直飘到过敏的人神经不停过敏,气喘的人一直气喘吁吁。
杨絮飘飘,转眼就飘过了一代人。
这是个心里总有泪,却不能哭出来的季节,后来渐渐习惯了堵塞的泪腺不再分泌液体。
夏天的时候出了车祸,破了些胆子,有的人就此遗忘了,有的人因此变得清晰,由此知道自己还是心胸狭隘,睚眦必报。
那些日子总在魂不守舍地游荡,总是不可抑制地心痛。
疼痛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自己。
暗夜里,总是不停地躺下,不停地坐起,有时是惊恐,有时是心悸,无论怎样的清醒,总是强迫症似的要去触摸每一寸痛感,自己的,亲人的。
父亲疼痛的时候依赖吗啡和多瑞杰,而我疼痛的时候拒绝任何药物,只希望疼痛来得更彻底一些,直到疼痛弥漫了所有的感受元。
只有刻骨铭心的疼痛可以医治疼痛,只有痛到最深处,痛到不能不麻木,我们终于不知道什么才是痛楚。
想起一个最笨的故事来,小时候住二宿舍,窗外种满花草树木,景致是美的,却抗不住夏天蚊子特别多,爬上树逮了土蝉回来放于帐中,依然有蚊子不停嗡嗡营营钻进来,索性忍着奇痒奇痛以身侍蚊,以血供奉,蚊子撑死了,叮咬自然终结了。
第三季逃离
流年似水,夏至刚来,一个人的日子就结束了。
面对现实,是最难面对的现实。
出走,是最好的逃跑。
从七月开始,每一次心跳,每一分脉动都在逃离中,云游,从海边到海边,从长城到长城,从深丘到内陆,从国内到国外。
重庆森林,到天津卫,山海关到角山倒悬的长城,塘沽湾的渤海到北戴河混浊的海水,然后是一次一次的上海滩。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好多话,说过了不用再说;有些人,告别了就不想再见;很多事,过去了就不再留恋。
生活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人往墙角逼,退无可退,只有迂回。
敌人源于内心,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跟对手作战,需要勇气;跟自己作战,需要恒久的毅力。
逃离,是快乐的,也是简单的;
逃离,是容易的,也是短暂的;
逃离,是心灵的逃难,看上去很美,觉出来很苦。
山水非不能寄情,只是不能长久地容身。
所以,天涯海角,再远,还是要回来。
我从地球的北面飞到太平洋的南边,纵使资本主义的乌鸦活得风生水起,资本主义的畜生过得风车斗转,咱还得千万里辗转,回来。
你别无选择,除了偶尔逃离。
在众多的目光中,我依然形销骨立,没有粮心,丢尽社会主义的脸面,但事实不容诋毁。
在光荣的第三季来临之际,体重终于增加了一些。
生活其实多不靠谱,爱情不靠谱,今天的承诺过了夜就成了狗屎一坨;权力也不靠谱,今天还颐指气使,明天就可能沦为牺牲的羔羊阶下的囚,贝布托死于炸弹也算死得其所;金钱也不是非常靠谱,没钱的人有贪欲,有钱的人易纵欲。
靠谱的东西大多单调乏味,让人也不想太靠谱。
然而,在诸多不靠谱的事物中,长胖是唯一可以用斤两作精确计算的,所以有必要大书特书,立此存照。
第四季改变
流年似水,流水有时候是有声音的,有时候,我们却听不见声音在变化。
中国戏曲当中讲究程式化,手眼身法步都有固定的意义,风雨雷电换一个手势就是兵戈铁马了。
戏曲发展到当代,依然整体延续,传统的程式、唱腔几乎一尘不变,变了,核就丢了,所谓创新不过是舞美灯光和服饰更靠近现代,而已。
生活不是中国古典戏曲,没有固定的模式,当生活已然开始向程式化靠拢的时候,生活已经变得可怕,活着基本等于不活。
当我这样的懒人都发展到被迫改变自己的时候了,生活实际已经可过可不过了。
心存希望,就寄念改变,挣扎一下,哪怕是垂死之前。
变,是脱胎换骨,所以纠结挣扎得厉害,生怕丢了核。
要放弃一些东西,却不能全放弃;
要面对一些东西,却想要背转身去;
总是不能坚持到底,坚持是一种能力。
我常常站在深夜的阳台看城市的夜晚,北京的冬天多是雾霭,怎么看都看不远,收回目光打量自己,也早已物不是人全非。
弗吉尼亚·伍尔芙关于生病有一篇经典的文章,感受身同。
病了一个月,从北国到南国,从南国再到北国,病体依然,拖着不经事的肉身,告别年。
流年似水,一切都已远走,握不住的,不喟叹,握住的,当珍惜。
第五季流年
流年似水,人在水一样的时光中浮动摇摆,粼粼波光中,恍惚而虚幻。
年头到年尾,一些人走了,一些人来了,一些人来了又走了,一些人走了又来了,一些人消失在风中,在雨中,在似水流年中。
只有文字,留存下来,每一个字,都在告诉我,所有的欢娱和不幸都跑到似水流年里去了。
赞赏
人赞赏
著名白癜风医院皮肤白癜风能治的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