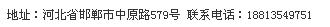苦双黄三
双黄
说明由于搞错了人物,在前文本意是写余姚妈及其母亲(即余姚外婆),却写成了余姚奶奶,只好修改,并重贴双黄(一)(二),双黄(三)在最后。带来阅读的不便还请谅解。
一
事情得从一个双黄蛋说起,它从狭窄的鸡屁股里落下来时,不偏不倚地落在余姚妈给垫的稻草上。余姚妈拿在手上的那一刻,基本就判断出它是个双黄蛋了。那个蛋温热,接近人体亲热后的体温,蛋壳沾上了些粪便,凝固了后却无减气味的新鲜。
她用塑料的胶勺舀了水仔细地清洗,像清洗一个婴儿。如果不是因为双黄蛋中的小鸡普遍发育不良,较为虚弱,破壳成为一道高高的门槛,她是不会把这个蛋从鸡屁股下拿走的。一想到大多数双黄蛋中的小鸡只能慢慢耗尽氧气,耗尽能量,见不到一丝光明就憋死壳中,她的心里就没有动恻隐之念,洗干净后敲开了蛋壳,果不其然蛋清铺满白瓷的碗底,蛋液包裹着两颗太阳一样的蛋黄,紧挨在一起,因为还没有成形,所以不知道是脸蛋挨着脸蛋,还是小嘴儿碰着小嘴儿。
她从挂在墙壁的筷子筐里取出一根,熟稔地搅拌起来,即令蛋清蛋液粘稠而密不可分,脸蛋小嘴密不可分,屁股内脏密不可分,它们足音轻轻地来过了,仿佛溪水在结冰之前,仿佛冰在刚刚融化之后,在分秒间以缓慢的姿态体会了一次人间。当她把筷子搁在瓷碗上,小鸡的羽毛收拢,皮肤寸解,鸡心鸡肝都不见形迹,依旧是白瓷碗里铺着黄色的蛋液。她舀了水在锅头里,两根筷子横放,白瓷碗平平地搁在上面,盖上锅头,便烧火蒸鸡蛋了。
她无疑是个巧妇,大锅头在她还是个小姑娘时,着实难为过她,使她在用烧火棍时呛出过眼泪,在洗锅头时气得想用抹布把每一滴水分擦干净。她把生命中所有好的不好的年华,全用来和一口锅战斗了,斗得啼笑也皆非,欲哭也无泪。她茫然而无措,没有人可以讲,从小姑娘到生了余姚的这些年,敬了一尊佛,请了一尊菩萨,对佛讲也对菩萨讲,佛和菩萨永远都是慈祥的脸,不发一语,如此她心里竟渐渐波平如镜了。那些俗事和烦忧惹起的一圈圈涟漪般的细纹,再也不轻易攀上她的眉头。
余姚妈不是嫁到余家来后,才知这里的偏僻地远。余姚妈也曾是娇嫩嫩的花,开得最好的那朵,蜜蜂嗡嗡地在她耳边飞。也不是每一句甜蜜的耳语都会让她惊喜地将花瓣绽放得更好,也不是每个人愿为牛粪的爱意都入得了她的眼。可她和余姚爸接吻的时候,尝到了比糖果更甜蜜的滋味,便死心塌地了。那时余姚的外婆极力反对这一门亲事,甚至将余姚妈锁在房中,上厕所也不让她出门,只给她一个尿壶解决。她干脆绝食,不吃不喝也不尿,躺在床上跟死尸一样。
到底是自己女儿,余姚外婆没有办法,抹着眼泪把她放出来了。余姚外婆张着一张没剩下几颗牙齿的嘴逢人就说,只怕余姚妈嫁到余家后没有亲故,受人欺负。她的一张嘴像一处伤口,敞开了净说催己泪下的话,旁人只好宽慰她,女儿就是割下的肉变泼出的水,留不住的。
余姚外婆在送嫁之时,当面给了余姚妈一套金器,抹着眼泪碎碎念叨着:“都说女儿嫁得远就是泼出去的水了,从此一别两地,难再相见。我把这套金器给你,是要别的人知道,你就算是泼出去的水,也是金水,莫让别人欺负了。”
余姚妈远嫁后,胸里总是起伏着,心跳紊乱,右眼皮跳个不停。她做了一个怪异的梦,梦里余姚外婆和邻居顶撞了几句,气得吃不下饭喝不下水。她在一旁照顾着,端起饭,喂也不是,哄也不是,急得团团转。她醒过来,汗濡湿了背脊的衣服,怎么也想不起来在梦中余姚外婆究竟因何事和邻居顶撞了,但猜测多半是为了她。
余姚爸给她一条毛巾擦汗,哄她别担心。他吻她的鼻子嘴巴脖颈锁骨,咬她的乳头,她扁平的腹部,她圆圆的肚脐。她原来不知道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俯身亲吻的,寸肌寸肤即以细密的一层汗珠回应,似曾幼时发一场高热的温度,似曾回到母亲腹中被温暖的羊水包裹。毛巾盖住她的躯体,扯开后能拧出汗。她的身体下过一场密雨,她不知道热带雨林的雨季是否有她的身体潮湿。这一刻她的身体觉醒了,她明白了女人的用处,这不坏,是实实在在的欢愉,她原以为世间林林总总多是空欢喜,于是便有些讶异虚空可以被进入被填满。
可这个梦境,一连三天都叫她惊醒,她还是没有听清余姚外婆和邻居顶撞了什么,还是猜测多半是为了她。余姚爸均匀的呼吸没有抚平她的神思隐忧,她没有找到那条擦汗的毛巾,想起来洗了晾在屋顶,便在黑暗中伸脚够到拖鞋,摸着楼梯扶手上楼顶。那夜的风很大,大得把毛巾吹走,只剩一个衣架空空地挂着;大得她燥热的躯体片刻起了鸡皮疙瘩,猝不及防地打了喷嚏,在第二天就着凉感冒了。小感冒喝些药就好,药劲使人困乏,她又连番做梦,醒来后想,莫不是余姚外婆病了。
她决定回家。余姚爸不许,也只好把她锁在房中,跟余姚外婆先前不许她成亲一样。她有了经验,故技重施,不吃也不喝,跟要嫁余姚爸一样,这回也坚定地要回娘家看余姚外婆。她毕竟是在娘家长大的,恬然地献出她的美丽,同时散发出一种奥秘的芬芳,花一样由余姚外婆用米汤牛奶喂养着,她能理解当初要远嫁时余姚外婆的眷恋和不舍。
她有些讶异于丈夫,怎么也对她生出了一番也要锁她不让她离开的情意。她的身体在多番调戏撩拨中已经开放过了,褪去的衣服像花叶褪去一层露水,与余姚爸的肌肤之亲献出了所有的敏感与高潮。她的身体如此,只是她还是没有明白,或者说没有体贴地顾及,如果她在新婚没几日就急着回娘家,余姚爸会多么怀念那广阔的空间和鼓翼而飞的情调。大抵女人都难以发现自身会丰溢到如何使男人瘫痪的地步,难以发现自身能让男人索取的欢乐是无可救药的。
她的理由足够恳切,锁在房中不吃不喝,她只好睡觉以抵抗饥饿,如此在梦中困得更深。她哭了,仿佛要把一生的眼泪都流尽。饿意和归意主导了她的意志,除此以外她感觉不到其他了,感觉不到身上还有五脏六腑,不仅血肉没有了,气体也要从她的体内漏出。她让余姚爸来摸摸她还有气不,吓得余姚爸哆嗦着手开锁,推门而入跪在她的床边,手摸摸她的鼻子,随后又捧起她的脸,凝视好久哭了。“我让你走,你吃饭吧。”余姚爸坐在床边喂饭,余姚妈吞下一口,说:“你莫怪我,我妈怕是不好了,活不长久了,所以在梦中着急让我回去。”
二
余姚外婆确实不好了,她在一夜之间丧失了语言能力,吐不出一句口齿清晰的话,也无法表达饿否渴否。尽管她努力地发出一些声音,却犹如风从树中过,叶子沙沙作响,掠过耳朵发梢,虽有声响而不成言语。
余姚外婆扶着墙,颤巍巍地踱向余姚妈,命运在那一刻发了一张交换牌,完全罔顾光阴已将她的两鬓染白,毫不留情地夺走她年久才修得的自顾能力,只手间遮住了她为人母的身份,令她在命终之前复又状若孩童。她的发病如同嗜睡了一回午觉,于日暮黄昏中终于迎回女儿,自深深处咧嘴笑了。原来将一切剥夺后让人老有所依,是命运赋予风烛残年之辈的最大看顾。
余姚妈的脸上还没褪去新婚的红晕,青春年华的列车上还留着她的座位,她本该在那个座位上多看些属于二十出头年纪的姑娘的好风景,仰起娇俏的脸,风吹起发丝时痒痒地刮着耳廓,冰雪为她消融,春天为她降临。但她毫不迟疑地搭上了要带走余姚外婆的列车,看见浓痰,看见血尿,在给余姚外婆洗澡时,数遍身上的老人斑。没有什么比照顾一个和自身美丽成反比的生命更能让人明白到,原来在青春之后是时时刻刻走向下坡路,走向幽黯的境况。
而服下的药物,它既不承诺老朽的身体再次康健,也不再提供多少喜乐的吉光片羽。谁都可以一眼看穿,比一日三餐更准时吞下的药片是生命的倒计时。
余姚外婆温文地接受了年华已逝,任由余姚妈喂她吃喝给她穿衣,要是想屙屎撒尿她就哼哼地叫。她有时会记得自己曾拥有过冷香凝脂般的大腿,记得油头粉面的小伙子们爱对她吹口哨,记得余姚外公吹牛皮特别厉害。有时候又什么都忘记了,看着群峦的侧影,忘记了在哪里有余姚外公的坟头,忘记了在那个坟头旁边,她也预备了自身的安葬之地。好在忘记了也不要紧,谁都知道她死了是要睡在余姚外公身边的。
她戴着的项链,心形挂坠里有一张小小的相片,神志不清以后,她手指哆嗦着打开看了好久好久,疑惑地想“这帅老头是谁呀”,老皱的皮肤里添了几道笑纹。她发出嗯嗯啊啊的模糊音节,像婴儿的笑语。笑语很快转为啼哭,她开始小便失禁,余姚妈不得不给她穿换尿布。
余姚外婆减龄般的每次退化都冲击着余姚妈的泪腺,她痛苦地呻吟,妈啊,你无法以自己血液的跳动去重新拾回时间了吗?她见到黑色的鸟群从地平线上蓦然振翼飞起,惊慌地关上了窗户,害怕鸟群是死神派来召唤灵魂的信使,故而急急捂紧余姚外婆的双耳,使她不听到这摄魂夺魄之音,好在人间多弥留半载。她害怕黑夜遽至或白昼降临之时,再也听不到余姚外婆嗯嗯啊啊的笑语或初生之胎一般的啼哭。她在过于沉寂以至听不到一丝声响的晌午时分,紧张地守护着余姚外婆的呼吸,心跳,脉搏。
岁月的小偷却最终窃走全部,它并不是敲锣打鼓而来,无情地闷声夺走人体最后的余温。在屋外的树荫下,依旧有人叫卖着五角钱一碗的凉茶,他们那“凉茶凉茶”的叫卖声,再也叫不醒余姚外婆,余姚外婆的嘴角也再也不会因为热气而溃烂。肉体沉寂着,无法喝下一碗茶,无法在继续流动的时间中重拾心跳和血脉。
季节正在转换,夏日的脚步已蹒跚,黄昏时分阵雨过后,大地的胚胎湿漉漉地孕育移栽于坟前的杜鹃,余姚外婆献身于长夏的炎阳之后,恬然安息埋于土壤。山雨从爱所愿,潮伏地面。余姚妈扶着杜鹃的枝干呕吐起来,所有的食物和胃酸从喉道涌出,她用脚尖蹭了些泥土覆盖住呕吐物,便虚脱了一般倚靠着树干,脊背出了一层细密的虚汗。她彼时还全然未知,那是余姚发出的第一个信号,是她的第一次孕吐。
三
回到暌违已久的余家,寒风已经占领了将要入冬的月份,没有燃烧得两眼直发黑的阳光,男人暂别温暖的天气,抱住女人的酮体久久地折腾。在寒冷的夜晚,床上漂着一个月光浴的女人,餍足多番,实属说得上淌了大部分男人一生中最多的柔情,似水一般可以溺泳。溺泳时,肉体和灵魂仿佛可以亲吻、触抚、交缠。这一种淋漓快意好比西瓜籽长在肉里,好比玉米粒从棒上剥落,爱情其实是瓜果粮食,其他无关宏旨。
不妨大胆想象,在月光之床漂浮着的人体,形成了一条肤色的饰带,见证造物和恩宠,焕发繁衍生息的神采,有伴侣之人才有幸为这条饰带缀以明亮的美好的如彩灯如花草之物。
当十月的脚步愈往后移,严寒更加冷冽,这条饰带就更为浩瀚。众多人类哼唱着季节的曲调,投身伴和肉体的对话,整个寒冬都消磨在耳鬓厮磨的欢笑声中,以双手为桨,身躯作舟,滑进了暖湿的水域,穿梭于狭窄悠长的水道。
谁都不愿意耽误良宵的分秒之时抬头看看天空中的灿烂辉煌,即使星星在冬夜尤其明亮。谁都无法叫那有韵律的拍打停顿,人间地面浩瀚的饰带,缀满了酮体,疯狂地竞赛着,在睡过的床诞下子女。
冬节,太阳几乎直射南回归线,这一天得到的阳光最为稀少,树上的鸟冻得收拢羽毛。余姚妈穿着一袭白色的长裙,张开双腿,从背后纤小的腰部到两腿,全都被汗湿透了。撕裂般的痛发出的叫声使一只路过屋檐的鸟几乎忘记飞翔,垂落快抵地面时才缓过神来,再次鼓翼而飞。
一坠落,一飞翔,屋内便响起了初生婴儿的啼哭。余姚妈的背脊还紧贴着床榻,黑色的秀发由于汗水濡湿而交互着一股股乱缠。她的眼角也在庞大的喜悦中湿成湖泊,湖中倒映着余姚爸接过婴儿后激动的洋溢喜悦的脸。
余姚爸俯身给余姚妈一个吻,这个吻让余姚妈无故想起余姚爸送给她的那个音乐盒。吻的动作还没有离开,余姚爸的手接踵抚上脸颊,替她轻轻推开乱糟糟地沾在脸上的头发,指尖轻挑撩拨至耳垂。这个动作像拧开了想象中的音乐盒的发条,音乐声却很真实地流泻而出,余姚爸在当中翩翩舞过床榻,舞过桌子,他怀里抱着的从她身上诞下的孩子,有一股芬芳,类似白色的茉莉。往后她的高耸的胸脯,将喂养这一朵茉莉,如同从前她的母亲喂养她馥郁地长大。
这一刻她想到母亲,这一刻她成了母亲。余姚妈先是耳朵灌进了音乐,接着眼睛也看见了余姚外婆长眠的山,目光越过石榴树和荔枝木的林荫深处,双脚近乎真实地走在羊肠小径,她的心奔向了自己母亲所在的彼处。
她才刚刚剪掉和孩子连结的脐带,却又重新长出了与余姚外婆连结的脐带。母亲长眠之处和女儿诞下之处,天边小股的红霞倏起,一直在整个天空中散布开来。
已故亲人坟前的鲜花遍野,在世之人夜里的情爱势如万钧,所有的大人都伫候在婴儿床旁。余姚妈无法描述那微妙的瞬间,对她产生的震撼和改变,她记得曾经跳过整个下午的舞,余姚轻悄悄地在婴儿床睡着了,她给她哼从前那个遥远下午跳舞时放的歌。
赞赏
人赞赏
南昌白癜风南昌白癜风专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