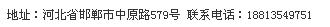乡情
秋的时令已过了一半,天空显得格外高远,望着田野间金黄的麦浪,已经远去的思绪又勾起我眷眷的思念。麦收时节曾是乡下最快乐的日子,收割、打场、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馒头,心中不自觉的萌生了满心的向往。收麦之后,于小院中、于瓜架下。支起一方木台,搭上一席木凳煮一盆青涩的毛豆,烫一壶陈年老酒,独斟慢饮,享受着因收获而澎湃的宁静,这是爸爸固有的专利。收割过后的田野,遗留下来的麦茬,星星点点散落的麦穗,等待着三三两两拾荒的人们。母亲自然也在这拾荒者之中。农活中,她最擅长的也就是这个。无拘无束,可多可少。清早我便跨上一个柳条编的篮子,迈着深深浅浅的步子,跟着母亲在新割的麦地里游移,逡巡着地上遗落的一颗穗、一粒麦。那时的天空是蓝色的,大地是金黄的,还有草坪上开着的野花,蚱蜢在草间倏尔起落。待到柳蓝里装满了收获,心中便盛满了喜悦。纵然鬓角挂满了汗珠,酸痛的双腿依然能够飞快的沐浴着晚霞回家,夕阳下,村落间炊烟袅袅升起,空气中弥散着庄稼桔的气息,心情美美的。众多的拾荒者中,妈妈算是个佼佼者,个子不是最高,体魄不是最壮,但拾得最多的往往是妈妈。那个年代,粮食短缺,拾些野菜,就着玉米面能不挨饿就是上等的生活了,如果能在麦收时节吃上一顿香喷喷的大馒头,呀,那真是奢侈的美味。这个时候,妈妈会将这一时期的战利品揉搓出麦粒,再将麦粒磨成黑乎乎的面粉,(舍不得去掉麦麸,所以面粉不像现在这样白)面粉发酵之后蒸上一锅大馒头,有桃形的、心形的,石榴形的。。。。。。石榴形的最好看,每每这个时候,我都会和弟弟去争抢。并以此为能。妈妈不识字,但很是擅长画石榴,她会不假思索的信手拈来,三下两下就会画出一个石榴,三刀两刀就会切出一个石榴,再加些点缀。很小的时候,看到她经常在地上画,我就会问她:画的是什么?她常会说:石榴。我说:真好看。这时候妈妈的眼里就会盈满了喜悦,自豪的说:当然了,姥姥家的院里有颗大石榴树,春天发芽,夏天开花,秋天结果,我九岁的时候就会坐在家中的石榴树上卖石榴。我说:你并不识字,怎么卖?妈妈说:客人拿走石榴,就会自觉地把钱放到篮子里,晚上只要把篮子带回家就中了。妈妈操着一口改不掉的乡音(山东话),说着这些的时候,似乎满树火红的石榴浮现在妈妈的眼前。眼里溢满了幸福的留恋。多年后,我带着幼子回到家乡,给妈妈带回了两个托人从外地带回来的石榴,妈妈细细品尝着,口中呢喃着:再不是当年的味道。漫步在家乡的田埂上,嗅着熟稔的炊烟,当年贫瘠的土地妩媚成金黄,田里再也见不到拾荒者的身影。爸爸已经故去。妈妈也已老了,沉重的篮子已不在轻盈。抬眼望去,天边晚霞依旧灿烂,浓浓的乡情从低矮的柴门里溢出,带着两代人童年的故事,飘向了天边,慷慨而去,来不及说声再见。
作者简介:网名蝴蝶飞舞时,原名刘桂芳,祖籍山东。内蒙古科左后旗甘旗卡第三中学语文教师。擅长散文、诗歌,追求诗文的理性、育化之美,语言的阳光、净化之美。代表作品:《飞向春天》、《梦里乡音》《秋日私语》《雪意》《校园的赞歌》《感叹流年》《秋之歌序列》《鹧鸪天》等。